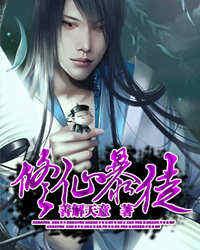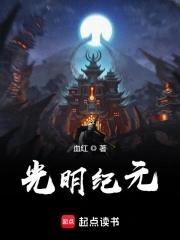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人在魔卡,策反知世 > 第204章 叶辉君这个大坏蛋就知道看她出糗加更1w(第2页)
第204章 叶辉君这个大坏蛋就知道看她出糗加更1w(第2页)
夜幕降临,银色光带渐渐隐去,D。Z。-X消失在视线尽头。孩子们陆续被家长接走,庭院重归宁静。只有风铃还在轻响,红绳网随风微颤,空胶卷盒发出细碎叮咚声,像是某种遥远频率的应答。
我和知世坐在廊下,谁都没说话。
许久,她忽然开口:“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合作拍短片的时候吗?”
我笑了,“当然。主题是‘消失的声音’,结果设备故障,录了一整天的电流噪音。”
“但我们还是把它提交了。”她眯起眼,像是回到那个夏天,“评审团说这是‘最具破坏性的诚实’。”
“后来那盘磁带被人借走了,再也没还回来。”
“我知道是谁拿的。”她低声说,“是一个参与过情感清洗项目的前工程师。他在三年后寄回一封信,说那段噪音让他想起了母亲临终前呼吸机的节奏,那是他唯一不敢录音的记忆。”
我怔住。
原来有些作品,不需要被理解,只需要被需要。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来自南极观测站残余节点的消息,加密等级极高,发送时间标注为“此刻”,接收终端却遍布全球。
内容只有一句话:
>**新信号源出现,频率匹配初代母版胶片波形。疑似D。Z。-X已抵达目的地,并开始回传数据。**
我猛地看向知世,“这意味着什么?”
她站起身,走向神龛后的暗格,取出另一件从未示人的装置??一块类似怀表的机械仪器,表面刻满古老符号,中央嵌着一小段仍在缓缓转动的透明胶片。
“这是‘叙事罗盘’。”她说,“D。Z计划最初的原型设备,能感应集体记忆流向的变化。如果D。Z。-X真的开始回传,它会指向新的锚点。”
她将罗盘放在石桌上,指针起初静止不动,几秒后突然剧烈震颤,继而缓缓旋转,最终停在一个方向??正对着神社后山的老电影院遗址。
那里曾是我们最早举办胶卷接力放映会的地方,如今早已荒废,藤蔓爬满墙壁,放映室窗户破碎,海报褪色成灰白轮廓。
“要去看吗?”我问。
她点头,“趁天还没亮。”
我们带上备用电源、便携投影仪和最后一卷可用的初代兼容胶片,徒步穿过林间小径。月光稀薄,树影交错,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声响,仿佛整座山林都在低语。到达影院门口时,发现门锁已被撬开,铁链垂落在地,像是有人比我们更早到来。
推开门,灰尘扑面而来。大厅座椅倾倒,幕布半塌,但放映室的灯竟然亮着。
我们对视一眼,缓步走上楼梯。
门虚掩着,透出微弱蓝光。推开门的刹那,我愣住了。
一台老旧的D。Z型投影机正在运行,型号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代都要原始,金属外壳锈迹斑斑,散热孔冒着淡淡白烟。胶片自动装载,运转平稳,没有任何人为操作迹象。屏幕上播放的影像并非来自任何已知资料库??
是一个女人坐在桌前写字的画面。
她穿着朴素的白衬衫,头发挽成低髻,笔尖在纸上沙沙移动。镜头固定,无配乐,甚至连翻页声都被刻意放大。持续了约五分钟,她停下笔,抬起头,直视镜头。
是知世。
但又不是现在的知世。她看起来年轻十岁,眼神更冷,嘴角紧绷,像是尚未学会如何微笑。她开口说话,声音经过滤波处理,却仍能辨认出本音:
>“如果你看到这段影像,说明‘记忆逆流’已启动。我是三年后的知世,通过D。Z。-X回传机制,将信息嵌入原始胶片层。请不要相信接下来七十二小时内收到的任何官方通告,包括自称‘系统妥协方案’的提案。那仍是伪装,它们正在学习以退为进。”
>
>“真正的威胁不是压制,而是收编。他们会推出‘共情认证平台’,让你上传私人记忆换取信用积分;他们会制造‘情感遗产信托基金’,承诺帮你保存一生的情绪数据;他们甚至会重建D。Z车站,宣称‘全民记忆共享新时代’开启……”
>
>“别信。这些都是陷阱。一旦个体记忆进入集中管理体系,自由意志就会被逐步稀释。你要做的,是让记忆保持流动,保持不完整,保持危险的真实。”
>
>“明天下午三点,旧市政厅地下档案馆将迎来最后一次开放。B-17号柜第三层,有一份未登记的纸质日志,记录着首批D。Z列车乘客的真实名单??不是编号,而是姓名、出生地、最后一句遗言。烧掉它,但在烧之前,用手机录下每一页。传播出去,越杂乱越好。”
>
>“还有……”她停顿片刻,神情软化,“告诉过去的我,不必害怕流泪。那不是弱点,是连接的证明。”
画面戛然而止,投影机随即断电,冒起一缕青烟,彻底熄火。
我和知世站在原地,久久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