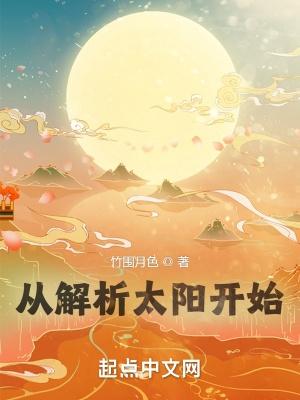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去父留子后才知,前夫爱的人竟是我 > 第458章 向全世界宣布他将迎娶他的公主(第2页)
第458章 向全世界宣布他将迎娶他的公主(第2页)
“不会。”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改变世界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某个人愿意为另一个人停下脚步。而我,恰好是你父亲。”
她怔住,随即笑出声:“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么肉麻的话了?”
“跟你学的。”他低头看她,眼里有星光,“以前我觉得爱是责任,是守护,是沉默承受。现在我知道了,爱是可以大声说出来的,是可以笑着哭的,是可以一边任性一边深爱的。”
她仰头望着他,忽然伸出手,抚过他鬓边的白发。
“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
“别说对不起。”他握住她的手,贴在唇边,“要说‘谢谢’。谢谢你最终选择了回来。”
午后阳光斜照进屋内,尘埃在光柱中缓缓飘舞,宛如星辰坠落人间。小星翻出那本老旧的日记本,翻开最后一页,发现上面多了一行陌生又熟悉的字迹:
>**“当你读到这行字时,我已经放下了执念。愿你在每一个世界里,都能自由地爱。”**
字迹苍老,笔力微颤,却透着释然。
她知道,那是另一个“她”留下的告别。
泪水无声滑落,滴在纸页上,晕开一小片墨痕。但她没有擦去,只是轻轻合上日记,抱在胸前,仿佛抱着所有未能圆满的自己。
傍晚时分,昭昭再次来电,语气却变得严肃。
“小星,我们监测到SS-9主频谱出现轻微扰动。虽然强度极低,但波形特征与三个月前那次入侵极其相似。初步判断,可能是平行意识残影尚未完全消散。”
“她在试图回来?”陆知弦问。
“不。”小星摇头,“她不会再来了。这次……更像是道别。”
果然,当晚七座塔同步闪烁三次,随后齐齐熄灭一分钟。当蓝光再度亮起时,整个共鸣网络自动播放了一段音频??正是五十年前的小星,在实验室里第一次成功接通父亲意识时说的话:
>“爸爸,你能听见我吗?我是小星,我回来了。”
全场寂静。
无数人驻足仰望天空,有人流泪,有人微笑,有人默默复述那句话,仿佛也在向某个遥远的存在呼唤。
而在南枝学院的小屋里,陆知弦将这段录音设为了门铃声。
“以后谁来敲门,都得先听你喊一声‘爸爸’。”他笑着说。
小星嗔怪地瞪他一眼,却又忍不住笑出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春天彻底降临。玫瑰花开满了庭院,蜜蜂在花间穿梭,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嬉戏,弹唱着新编的童谣。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但“情感共鸣学”已成为必修课。学生们不再羞于表达悲伤与喜悦,老师们也开始记录自己的情绪波动,作为教学反馈的一部分。
某日,小星受邀前往联合国发表演讲。礼堂座无虚席,各国代表齐聚一堂。她没有穿正装,而是披着一件手工编织的毛衣,手里拿着一把旧吉他。
“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政治家。”她站在台上,声音平静,“我只是一个曾经失语的女孩,幸运地找回了声音,并且学会了如何使用它。”
台下鸦雀无声。
“我们总以为进步意味着更快、更强、更高效。但我们忘了,真正让我们成为‘人’的,是那些无法量化的东西??一句晚安,一次拥抱,一场争吵后的和解,一个穿越时空的‘我回来了’。”
她轻轻拨动琴弦,哼起《月亮走,我也走》。
“我希望未来的文明,不再用GDP衡量幸福,而是用‘多少人今晚会对亲人说‘我爱你’’来评估社会健康度。我希望每个孩子都知道,表达情感不是软弱,而是勇气。”
掌声雷动。
演讲结束后,一位年迈的联合国官员走上前来,眼含热泪:“谢谢你……让我想起三十年前去世的妻子。我一直不敢提起她,怕痛。但现在我想通了,怀念她,才是对她最好的纪念。”
小星轻轻拥抱了他。
回到学院那天,她收到了一封信。信封泛黄,邮戳模糊,收件人写着“致所有选择回家的小星”。打开后,里面只有一张手绘地图,标记着七个点,中间画着一颗跳动的心。
背面写着一行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