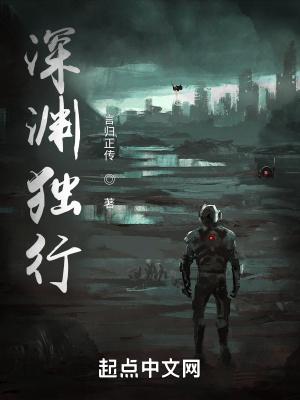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激情年代:开局成为七级工程师 > 第三十九章 一九七四(第2页)
第三十九章 一九七四(第2页)
“这不是技术。”林远喃喃道,“这是记忆本身在选择传递方式。”
那一整天,他们谁也没再提盒子里的事。可村里人似乎都察觉到了什么。午后的风变得温柔,孩子们不再追逐打闹,老人坐在竹椅上闭目养神,仿佛整个村庄都在无声地守灵。
傍晚时分,一个陌生女孩出现在村口。她约莫二十出头,背着画板,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磨破边的帆布鞋。她找到林远家门前,犹豫片刻,才开口:
“请问……这里是林远老师住的地方吗?”
“我是。”林远走出来。
女孩深吸一口气,从画板下抽出一幅油画。“我叫周念。”她说,“我是……周明璃的侄女。”
林远愣住了。
苏岚接过画,展开一看,画面中央是一座透明纪念馆,玻璃地板下流淌着幽蓝光芒。四周漂浮着无数名字,其中最亮的一个,正是“周明璃”。而在馆外山坡上,一对男女并肩而立,仰望着升腾的光点??那分明是林远和苏岚的背影。
“这画……你什么时候完成的?”苏岚问。
“三个月前。”周念低声说,“那天夜里我突然醒来,脑子里全是这个场景。我没见过姑妈,但她在我梦里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七个女人如何用沉默撑起一座桥,又如何在人们重新学会流泪的时候,安静地退场。”
她顿了顿,声音哽咽:“她说,如果有一天我把这幅画送到你手上,就代表她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林远久久无言,最终只是轻轻点头,将她请进屋。
那一晚,三人围坐在灯下,听周念讲述她这些年的生活。她原本学人工智能,但在一次情绪模拟测试中,系统判定她“共感指数偏低”,建议进行神经调节干预。她拒绝了,并主动退出项目组,转而投身行为艺术与记忆可视化研究。
“我发现机器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在看完一场雨后哭出来,明明天气预报说这只是普通降水。”她说,“但我懂。因为那场雨,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姑妈给我念诗的声音。”
临睡前,林远独自走到屋后山坡,抬头望天。星空清澈,银河横贯,仿佛一条未被编码的古老河流。他忽然想起大学时代和周明璃的一次对话。
那时他们刚完成共感网原型设计,兴奋得彻夜未眠。
“你觉得未来的人会更幸福吗?”他曾问她。
她靠在实验室窗边,看着凌晨三点的城市灯火,淡淡地说:“我不关心幸福。我只希望将来有人能在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偷偷为一朵花掉眼泪,然后继续走路??并且知道,那滴泪,属于自己。”
如今,那样的人越来越多了。
第二天清晨,周念留下画作离去。林远站在村口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山路尽头,心中竟无太多离愁,反倒有种奇妙的圆满感。
几天后,一封匿名信寄到了家里。信纸是手工压制的,带着植物纤维的纹理,上面只有一句话:
>【谢谢你,让我们死得像个活人。】
没有署名,邮戳来自青海某偏远小镇。
林远将信纸夹进日记本,合上封面。他知道,这句话不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从所有曾被系统抹去声音的灵魂深处,共同涌出的一声叹息。
时间继续向前。
半年后,“断链学校”迎来第一批毕业生。他们在毕业典礼上不做演讲,不颁奖项,而是集体完成了一场“静默仪式”:每人写下一件从未与人分享的秘密,投入火盆焚烧。火焰升起时,没有人拍照,也没有人追问内容。他们只是静静地看着灰烬随风而去,如同送别一段私密的成长。
有个男孩在事后悄悄告诉林远:“我写了我曾经嫉妒妹妹夺走了父母的爱。烧完之后,我觉得心里空了一块,但很干净。”
林远拍了拍他的肩:“那就是自由的感觉。”
与此同时,全球“记忆储蓄池”的访问量持续下降,但个体情感表达质量显著上升。社交媒体不再追求瞬时热度,取而代之的是“慢共感平台”兴起??用户需等待48小时冷却期才能发布情绪记录,期间系统不会推送、不会分析、也不会生成标签。
人们开始习惯等待。习惯在愤怒之前先呼吸三次,习惯在悲伤之后独处一晚,习惯在快乐时不必立刻找人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