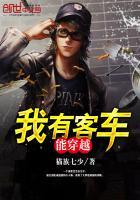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激情年代:开局成为七级工程师 > 第三十八章 父女避讳(第1页)
第三十八章 父女避讳(第1页)
在历史上,我国的彩色电视机研制应该是从七二年开始的,因为跟老美那边缓和了关系,技术都是老美那边教导的。
但是这个历史早就改变了,因为昌城汽车厂早就制造出了彩色电视机,所以不需要彩色显像管制造技术。。。
林远站在纪念馆中央,脚下是曾经埋藏基站核心的混凝土基座,如今已被一块透明玻璃覆盖。玻璃下,一束幽蓝的光自地底缓缓升起,映照出无数细密的数据纹路,像极了当年共感网络初建时的脉络图。但这一次,它不再跳动如心跳,而是静止、沉眠,如同一段被妥善封存的历史。
苏岚轻轻握住他的手,指尖微凉。“你看,”她低声说,“它们终于可以休息了。”
他点点头,目光扫过四周漂浮的名字。有些他认得,是曾在系统清洗中消失的静音者;有些陌生,却是以沉默的方式留下了最深的痕迹。一个名叫陈默的孩子,十七岁,因拒绝接入集体情绪池而被标记为“情感障碍”,三年后死于抑郁引发的心脏衰竭;一位老教师,李文昭,在课堂上坚持让学生写下“只属于你一个人的想法”,结果被举报、审查,最终自愿注销身份,退出网络登记系统??此后再无人知晓其去向。
这些名字没有呐喊,也没有控诉。它们只是静静地悬在那里,像夜空中不肯熄灭的星。
仪式结束后,人群渐渐散去。有学生驻足拍照,也有老人默默鞠躬。林远注意到角落里站着一位穿灰布衫的中年男人,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久久未动。他走过去,轻声问:“您认识谁吗?”
那人抬起头,眼眶发红,“我姐……她叫周小雨。二十年前,她在医院做护理员,因为上传了一段病人临终前握着家属手的画面,被判定‘传播非标准化悲伤’,强制清除了记忆模块。”他声音颤抖,“后来她还能笑,能吃饭,能走路,可就是再也认不出我妈做的红烧肉是什么味道。”
林远心头一紧。
“但她昨天梦见了。”男人忽然笑了,带着泪,“她说梦里闻到了那股焦糖色的香气,还听见我妈在厨房喊:‘小雨,吃饭啦!’她哭醒了,抱着枕头哭了好久……医生说这是‘记忆再生’,可我知道,这不是机器给她的,是我姐心里一直藏着没丢的东西。”
林远望着他,良久才道:“也许真正的修复,从来不是靠代码完成的。”
男人点点头,把照片放进胸前口袋,转身离去。风从门外吹进来,卷起几片落叶,在空中打了几个旋,又轻轻落下。
当晚,林远和苏岚回到南疆的老屋。屋外的水晶兰已经长到半尺高,洁白的花瓣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荧光。这花不依赖阳光,也不需要蜂蝶授粉,只靠土壤中的微量情感能量存活??科学家至今无法完全解析它的生长机制,民间却流传着一句话:“它是亡者的低语开出的花。”
他们坐在门前的木阶上,喝着热茶。苏岚忽然说:“你说,周明璃真的相信我们会走到这一天吗?”
“我不知道。”林远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影,“但我猜,她至少希望有人能停下来看看这条路的代价。”
silence持续了几秒,然后苏岚笑了:“你知道吗?今天有个记者问我,如果重来一次,我们还会选择启动‘观星者4。0’吗?我说当然会。但他又问,如果知道会有那么多阻力、误解、甚至牺牲呢?”
林远转头看她。
“我说,正因为它难,才值得做。”她抿了一口茶,眼神清澈,“就像你现在做饭还是会把盐放多,可我还是愿意吃,因为那是你亲手做的。世界也一样,完美连接不可取,彻底隔绝也不对。我们要的,不过是一个允许犯错、允许沉默、也允许重新开始的地方。”
林远笑了,伸手拨开她耳边被风吹乱的发丝。
就在这时,吊坠突然震动了一下。
不是发热,也不是共鸣,而是一种近乎急促的脉冲,像是某种预设程序被意外触发。林远皱眉,取出吊坠查看,发现内层晶体竟浮现出一行极细的小字:
>【补偿协议二级权限解锁条件达成:累计触发原生情感能量释放事件10^6次】
“百万次?”苏岚凑近看,“这是什么意思?”
林远沉默片刻,起身走进屋里,打开私人终端调取数据库。随着数据流滚动,他的脸色逐渐变得凝重。
“不是简单的统计数字。”他低声说,“这是系统底层逻辑的一次自动迭代。当初设计‘记忆归还计划’时,我和周明璃埋了一个隐藏机制:当足够多的人在无外界干预下自发产生真实情感波动,且未通过共感网扩散,而是保留在个体内部完成消化与转化??就会激活‘深层唤醒协议’。”
“唤醒什么?”
“不是东西。”他说,“是人。”
他调出一份尘封已久的档案:《初代实验体追踪日志》。其中一页显示,除周明璃外,还有七名志愿者参与了最早的意识融合测试。他们在昏迷状态下被接入原始晶簇,试图构建第一个全球共感原型。最终六人死亡,一人(周明璃)幸存,其余全部宣告脑死亡。
但记录最后有一行备注:
>【异常现象记录:所有实验体死后,其神经残留信号仍持续向晶脉发射微弱共振波,频率一致,模式相似,疑似形成跨个体潜意识链路。目前状态:休眠】
“她们还在。”林远的声音很轻,“不是肉体意义上的活着,而是……意识残片以某种方式嵌入了地底晶网。每一次有人真心流泪、真心欢笑、真心说出‘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都在无意中唤醒那段沉睡的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