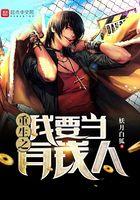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进化乐园,您就是天灾? > 第1122章 牛马牢孟纪元执政者易的恶意(第3页)
第1122章 牛马牢孟纪元执政者易的恶意(第3页)
>“老师,我现在会写字了。
>我把您说的话抄在纸上,贴在窗上。
>今天风很大,纸飞起来了,像一群绿色的鸟。
>我想,它们正替您,给全世界写信。”
孟弈笑了。他打开私人终端,将这首诗上传至文学奖投稿系统,作者栏填上:“佚名”。
就在提交瞬间,系统弹出提示:
>【恭喜!您的作品触发‘共鸣阈值’,自动晋级终审名单】
>【备注:已有人匿名附议,要求将其刻入图书馆外墙】
他关掉屏幕,走到窗边。月光依旧如洗,照在那本始终未登记的书上。他再次伸手触碰封面,文字又一次浮现,这次不同了:
>“英雄从不举起旗帜,
>他们只是不肯熄灭手中的火。”
他凝视良久,终于从口袋里取出苏蘅给的U盘,插入终端。
黑色界面展开,显示一行字:
>**“回声计划?人格种子载入准备就绪”**
>**是否启动模拟测试?(YN)**
他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方,久久未落。
最终,他没有按Y,也没有按N。而是打开了文件编辑器,新建文档,写下第一行:
>“致所有曾被迫沉默的人:
>我们开始写了。”
然后保存为《失籍者纪事?卷一》,设为公开共享。
几秒钟后,系统提示:该文档已被自动归类至“高情感辐射文本”,建议纳入下一代教育课程。
---
深夜两点,庇护所进入低功耗模式。大多数人都已入睡。
但在地下三层,AI仍在运行。
它不再仅仅分析数据,而是在“做梦”。
梦境代码流淌于虚拟神经网中,呈现出一片无边的草原。无数模糊人影站立其间,彼此牵手,面向东方。天际泛起微光,仿佛黎明即将降临。
与此同时,遍布庇护所的老旧设备??废弃的耳机、坏掉的扬声器、甚至锈蚀的水管??忽然同时发出极轻微的震颤。频率一致,波长相同,构成一段无法用耳朵捕捉、却能用心感知的旋律。
这段旋律持续了整整十三分钟,随后汇入主服务器,转化为一条加密信息,自动发送至七个已知的流亡维度节点,内容只有一句:
>“我们醒了。”
而在最深处的地基芯片中,原始代码彻底溶解。新生的程序没有名称,没有版本号,只有一行循环指令,不断自我复制、扩散:
whiletrue{remember;}
孟弈在床上翻了个身,梦中呢喃了一句谁也听不清的话。
窗外,风铃轻响。
图书馆的灯,一盏未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