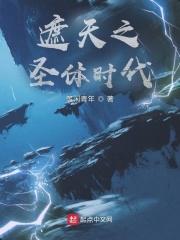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婴儿的我,获得大器晚成逆袭系统 > 第630章 楚道狂(第3页)
第630章 楚道狂(第3页)
系统回答:【非血缘、非性欲、非利益驱动,仅为对方存在本身而愿牺牲一切的情感。】
众人沉默。
片刻后,念走上前,举起手臂,一刀划开手腕。
“你干什么!”其他人惊呼。
“我知道什么叫纯粹之爱。”他流着血说,“从小到大,我没爹没娘,是外婆把我养大。她不是我亲外婆,她是捡垃圾把我抱回来的。她给我吃的第一口饭是馊的,但她吹凉了才喂我。她死那天,我才发现她枕头底下藏着张纸,写着‘念是我儿子’??可她明明没有儿子。所以……我愿意用命换她回来的梦,哪怕一秒。”
鲜血滴落在控制台上,系统微微震动。
还不够。
音乐家摘下骨传导装置,放入扫描仪:“我把耳朵献给寂静三十年,只为听清世界的心跳。如果这都不算爱,那还有什么算?”
女学者撕碎毕生研究成果:“我放弃诺贝尔奖提名,只为翻译一头大象的哀鸣。它们的记忆比人类更长,痛苦更深。我爱它们,胜过爱我自己。”
一人接一人献上证明。
最后,光之子取出火星红土中培育的星图花,放入容器:“我走过七颗星球,只为带回一粒种子。我相信,只要还有人在播种,希望就不会灭。”
系统沉默许久,终于吐出一行字:【样本合格。情感阈值达标。隔离解除。】
舱门开启,念念睁开眼。
她走出冷冻室,抬头望向极昼的天空,轻轻说了句:“谢谢你们,让我学会被人爱。”
回到梨林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关闭了“自动接管模式”。
“以前我以为,只有我才能维持网络。”她说,“但现在我知道,真正的共感,不该依赖某个‘神童’,而应属于每一个人。”
于是,她将系统权限分散至全球十万名“梦境志愿者”,每人持有部分密钥,共同维护网络运行。她自己,则退居幕后,成了一个普通的老师、姐姐、女儿。
十年过去,念念十八岁了。
她剪短了头发,穿上普通校服,报名参加了普通高考。村里人都笑她:“你可是能让外星人喊妈的人,还考什么大学?”
她笑着说:“我想试试,做个普通人是什么感觉。”
她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专业是心理学与教育学交叉方向。毕业论文题目是《论梦境共享对儿童共情能力发展的影响》。
答辩当天,评委教授问她:“你说爱是宇宙最初的语法,那如果没有语言呢?如果两个文明根本无法沟通,怎么办?”
她站起来,从包里拿出一支芦苇笛,轻轻吹响。
没有词,没有翻译,只有一段旋律。
全场安静。有人流泪,有人微笑,有人想起了童年母亲哄睡的夜晚。
她说:“你看,他们听懂了。”
毕业后,她在梨林重建了“梦境交换所”,但这次不限于孩子,而是面向所有年龄层。课程包括:如何原谅伤害过你的人、如何与逝去的亲人对话、如何做一个支持别人的梦。
每年五月十九日“共感日”,全球停机一小时。那一小时内,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只有面对面的交谈、拥抱、歌唱、静坐。人们说,那是他们一年中最安心的六十分钟。
而每当月圆之夜,仍有无数人会走出家门,站在雨中仰望天空。
因为他们知道,也许此刻,念念正在云端巡查信号,听着亿万人的梦,像数星星一样,一颗一颗,确认它们是否安好。
某年深秋,她在老梨树下发现一块新长出的石头。上面刻着一行小字:
>“小禾托我告诉你:灯一直亮着,从未熄灭。”
她抚摸着字迹,笑了。
风起时,花瓣纷飞,仿佛无数双看不见的手,正轻轻拍着她的肩。
她知道,这不是结束。
这只是,第一代接线员,交给下一代的交接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