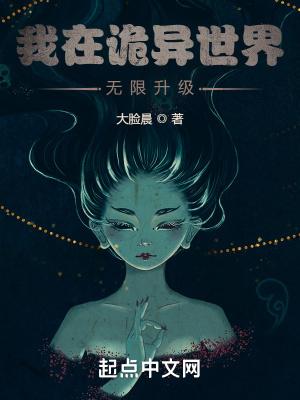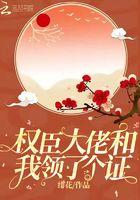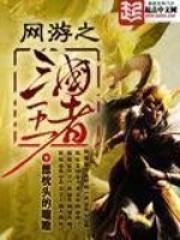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朱元璋的官,狗都不当 > 第二百一十三章 运河贯通(第3页)
第二百一十三章 运河贯通(第3页)
夏六月,天气炎热,京城疫病初起。朱允?果断下令关闭坊市三日,派遣太医署全员下乡施药,并启用战时体制调运粮食。同时,他打破惯例,允许民间医生参与防疫,凡献有效方剂者,赏银五十两。
此举极大激发了民间智慧。一位苏州女医研制出“避瘟香囊”,内含苍术、菖蒲、雄黄,佩戴即可防病,迅速推广全国。朱允?亲题“济世仁心”匾额相赠,并破格授予她“太医院名誉待诏”之职。
秋七月,西北再传捷报:甘肃总兵率军深入戈壁,剿灭最后一批“靖”字残匪,缴获大量武器辎重,其中包括西洋火枪与葡萄牙地图。经审俘得知,这批军火系经马六甲走私而来,幕后买家正是“白翁”。
朱允?立即召见葡萄牙使节,严正声明:“尔等若继续资助叛逆,大明将封锁澳门,断绝贸易。”葡人惶恐谢罪,承诺彻查商团,并协助缉拿“白翁”。
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传来好消息:三位曾意图祭祖的藩王,经朝廷晓以利害,已主动撤回申请,并联名上表支持《忠烈纪念日》设立,称“愿世代铭记壬午忠魂”。
朱允?欣慰之余,仍不忘警示:“藩王归心,非因威压,而在道义。只要朝廷持正,天下自服。”
冬月初一,阿禾终于来了。
她不再是那个冻得通红的小女孩,而是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女,穿着粗布棉裙,手里提着一盏比去年大出三倍的莲花灯,灯面上写着:
**“皇上爷爷,我学会写字了。我要做女先生,教孩子们讲真话。”**
朱允?站在钟楼下,望着她一步步走近,眼眶湿润。
“你迟到了。”他笑着说。
“路上帮婆婆挑柴,耽误了一会儿。”阿禾抬头,眼神清澈如泉,“但我每年都来看您点的灯。它一直在那儿,风吹不灭。”
朱允?接过她的灯,挂在飞檐之下,与自己的那盏并列。
当晚,他破例允许阿禾留在宫中用膳。席间,小姑娘毫无拘谨,滔滔不绝讲起村里的变化:沟渠修好了,私塾免费了,连妇人也能报名识字班。“先生说,这都是因为有个叫建文的皇帝,曾经为我们活过。”
朱允?听着,笑着,心底却涌起一阵酸楚。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一生最大的成就,或许不是夺回皇位,也不是清算旧账,而是让一个普通农家女敢于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过一位不愿欺压百姓的皇帝。
腊月廿三,小年夜。朱允?再次登上钟楼,这一次,身边站着阿禾。
两人并肩而立,望着满城灯火。远处河面上,无数河灯顺流而下,宛如星河倾泻人间。
“阿禾,”朱允?轻声问,“你说我是好皇帝,可将来别人骂我怎么办?”
少女认真想了想,说:“那就让他们骂。只要还有人记得您做过的事,光就不会灭。”
朱允?笑了,眼角皱纹舒展如春水。
他取出一枚新的建文通宝,递给阿禾:“拿着吧。等你成了女先生,把它挂在学堂门口。告诉所有孩子??”
“??我见过那个皇帝,”阿禾接过铜钱,郑重地说,“他给我点过灯。”
风起,两盏莲花灯在夜空中轻轻碰撞,烛火交映,如同两颗跳动的心。
朱允?仰望星空,喃喃道:
“老师,您看到了吗?
道没有绝,光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