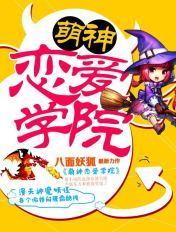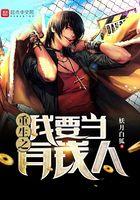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综武侠]肝露谷,但快意江湖 > 26818二更(第2页)
26818二更(第2页)
可谁敢承担这份重负?
谁又能决定,哪些记忆该被转移,哪些该留下?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际,念溪站了出来。
“我来。”她小小的身体站在烛光下,异常坚定,“我妈忘了我,可我记得她。我奶奶忘了自己是谁,可我记得她说的话。我想替更多人记住,哪怕会痛。”
小荷望着她,眼中泛起泪光。
仪式在第七十三口井举行。
月圆之夜,七十二盏金灯围成环形,忆引铃悬于井口,随风轻颤。小荷盘坐中央,手持新笛,吹奏《释忆谣》??一首专为记忆转移而创的曲子。音波如丝,将她体内纷繁的记忆抽出,化作点点荧光,在空中交织成无数画面:战火中的母亲、雪地里的士兵、沙丘上的祭司、铁箱中的木牌……
念溪闭目静立,双手合十。
当第一缕光触碰到她额头时,她浑身一震,像是被千万根针刺穿。但她没有退缩。
一幅幅画面涌入脑海??她看见自己真正的父亲被拖出家门,母亲抱着她躲在灶台后瑟瑟发抖;她听见奶奶临终前喃喃:“别让他们改我的名字……我是林婉娘的女儿……”;她甚至感受到小荷每一次吹笛时内心的挣扎与孤勇。
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滴入井中,激起一圈涟漪。
三日后,仪式结束。
小荷醒来,黑纹消退大半,但左耳失聪,再也听不见高音笛声。而念溪虽保住性命,却失去了自己童年前三年的记忆。她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学会走路的,也不记得第一个叫她“宝贝”的人是谁。
但她记得所有不该被遗忘的事。
她成了最年轻的“执忆使”,每日穿梭于忆疗所与千忆阁之间,为失语者翻译梦境,为无名者命名立碑。孩子们围着她喊“念溪姐姐”,她总是笑着递上一杯桂花蜜,说:“先喝点甜的。”
又一年清明。
思源节正式成为全国庆典。街头巷尾挂起红灯笼,上面写着一个个平凡却珍贵的名字:李三娘、赵承业、阿兰朵、林婉娘……百姓自发在门前摆放小碗甜汤,纪念那些曾因爱而勇敢的人。
小荷坐在井边,用单耳听着风中的笛声。
凌寒站在她身旁,忽然说:“我想去极北之地看看。”
“那里还有什么?”
“有人说,最后一粒清梦核的碎片,可能沉在万年冰渊之下。它不再害人,却仍在低语??不是让人忘记,而是在学着记住。就像一个濒死的怪物,临终前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痛。”
小荷点头:“那就带它回来吧。不必毁灭,可以封存。让它听着人间的笛声,慢慢变成石头。”
凌寒笑了,第一次笑得如此轻松。
阿满跑来,手里拎着刚出锅的糯米团子:“趁热吃!我按你娘写的时辰蒸的,整整三刻钟!”
阿芸抱着新抄的《禁录》续卷走进来:“这一册,全是孩子们写的。他们说,要把爸爸妈妈讲过的故事都记下来,免得将来没人信。”
念归倚在门框上,咳了几声,却眼神明亮:“老夫打算写本《忆政通鉴》,专记那些史官不敢写的真事。第一篇,就叫《小荷吹笛之夜》。”
小荷低头,看着井水。
水面倒影中,不再是母亲的脸,而是许许多多面孔的叠加:有哭泣的、微笑的、怒吼的、低语的……她们都在看着她,像星辰注视大地。
她举起笛子,轻轻吹起《糯米团子歌》。
这一次,不止是风在听。
远处山坡上,一群孩子手拉着手,跟着旋律哼唱起来。
歌声飘向四方,落入新开的井中,唤醒沉睡的花根;钻进老者的耳中,让他猛然记起亡妻最爱的发簪样式;传进皇宫深处,让那位曾依附清梦核的老太监,在弥留之际喃喃道出自己原名:“……阿福。我本名叫阿福啊……”
桃花纷飞,如雨落下。
而在东海某座无人知晓的小岛上,一块新立的石碑静静矗立,上面刻着两行字:
>“此处曾无人记得。
>今始有声。”
风起了。
笛声未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