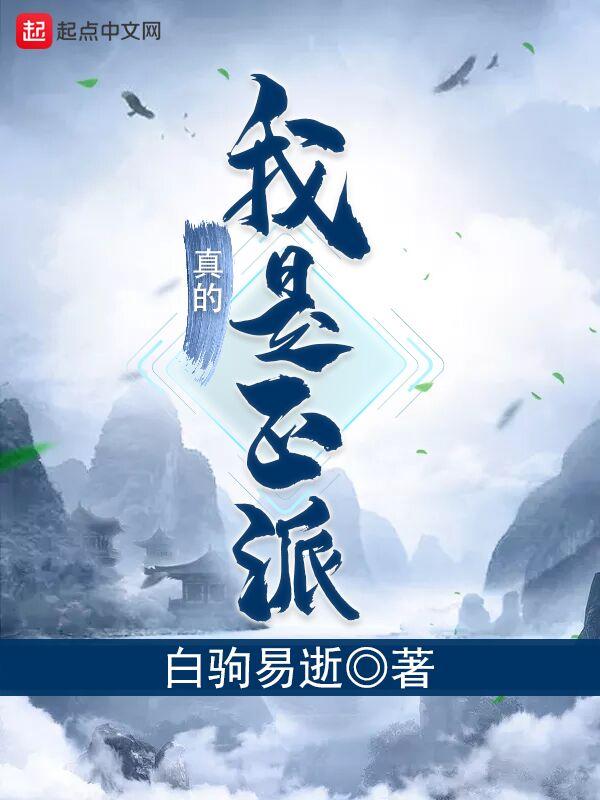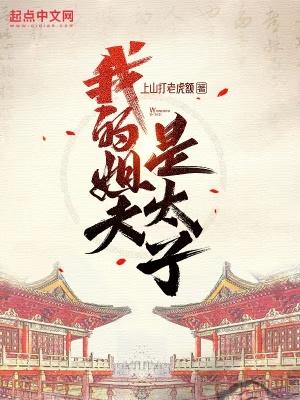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一人之上清黄庭 > 第八百七十一章战后(第1页)
第八百七十一章战后(第1页)
花果山?天真顶,洞开裂缝。
刷!
点滴兵器交戈之声,汇聚成潮。
周天星辰大阵中的新星官们,拿出了自己的武器和法宝,气势汹汹,严阵以待。
所有人紧盯着虚空洞口,眼大如铃,心跳打鼓。。。
风从黄庭学院的草坡上掠过,带着非洲春夜特有的温润气息。少年坐在篝火旁,火光映在他脸上,像一层薄薄的金纱。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学生们围坐成圈,彼此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一个来自刚果的女孩正低声说着童年时目睹村庄被焚毁的那一夜,她声音颤抖,却坚持不中断。她说完后,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安慰,只有片刻沉默,然后下一个学生轻轻接过了话头:“我想告诉你,我听见了。”
这样的夜晚,在这里已是常态。
少年低头看了看腕上的青纹,它依旧存在,但已不再跳动如初。它的颜色淡了许多,像是被岁月洗过的布料,却更加沉静。他知道,这道印记正在完成一次缓慢的转化??从外来的启示,变为内在的沉淀。就像那些曾经依靠他引导的人,如今已能自己点燃灯火。
远处传来脚步声。一名年轻助教走来,递给他一部老旧的卫星电话。“刚收到‘清醒站点’的消息,”她说,“西伯利亚那个女孩……醒了。”
少年抬眼,目光微动。
“她醒了?”他问。
“是的。而且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他回来了吗?’”
少年沉默片刻,将电话轻轻放在膝上。他知道她说的是谁??不是医生,不是科学家,而是那个每天陪她画图、听她讲蒸汽火车与地下矿脉歌声的人。是他曾用倾听唤醒了她体内某种古老而沉睡的东西。
“她还记得我?”他轻声问。
助教摇头:“她没说名字。但她画了一幅新的图。他们把图像传来了。”
她打开平板,屏幕上是一幅复杂交错的线条网络,中央是一个巨大的螺旋结构,周围环绕着十二个支点,每个支点都连接着不同形态的能量流。地理专家初步分析后认定,这张图描绘的竟然是全球主要地震断裂带与人类情感共振热点的叠加模型。更惊人的是,其中三个区域已被标记为“即将苏醒”,时间精确到日。
而这三处地点,恰好是尚未建立“黄庭联络站”的空白区。
少年凝视良久,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得意,只有一种近乎宿命般的了然。他终于明白,那女孩不是病人,也不是偶然觉醒的特例。她是“回声环”的自然产物,是当孤独被持续倾听之后,心灵所进化出的新感官。她听见的,不只是土地的声音,更是整个星球的情绪脉搏。
“准备出发吧。”他说。
三天后,他踏上前往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旅程。那里有一座被遗弃的矿业小镇,三十年前因一场神秘塌方全员撤离,此后无人敢入。最近两个月,却有徒步者报告称,在深夜能听到镇中传出合唱声??几百个声音齐唱一首无人知晓的歌谣,歌词模糊,旋律却异常和谐。
联合国派出的探测队进入后全部失联,七十二小时后才陆续走出,神情恍惚,口中反复呢喃同一句话:“我们本来可以不死。”
“清醒站点”判定这是集体记忆潮汐引发的认知污染,建议封锁该区域。但少年知道,这不是污染,而是呼唤。
他在边境小镇雇了一名向导??一位年迈的克丘亚族老人,曾是当年矿难幸存者之一。老人见到他的第一眼就跪了下来,老泪纵横:“你来了……我就知道你会来。她们一直在等你。”
“谁在等我?”少年问。
“那些没能走出去的女人和孩子。”老人哽咽着说,“那天塌方前,她们在教堂排练复活节的颂歌。可男人全被调去主坑抢险,没人听见她们的歌声。后来山体闭合,声音就被封在里面了……几十年了,她们还在唱。”
少年心头一震。
当晚宿营时,他翻开笔记本,写下一行字:
**“有些声音不会消散,因为它们从未被真正听过。”**
次日清晨,他们抵达小镇入口。荒草淹没街道,房屋半塌,唯有那座石砌教堂仍屹立不倒,屋顶破了一个洞,阳光斜射进去,像一道审判的光剑。少年缓步走入,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的灰尘与潮湿木料的气息。祭坛前,一本残破的乐谱静静躺在地上,纸页泛黄,边角焦黑。
他蹲下身,轻轻拾起。那是《圣母颂》的手抄本,但在副歌部分,有人用铅笔添了一段陌生旋律,旁边写着一行小字:“给所有没被救走的孩子。”
他闭上眼,将乐谱贴在胸口。
刹那间,耳边响起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