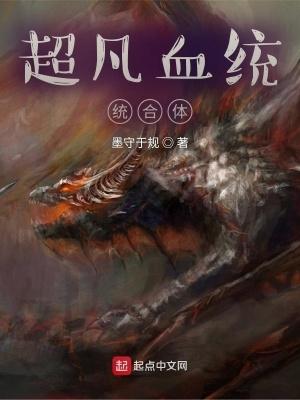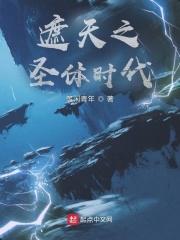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旧时烟雨 > 第六百一十三章 你醒啦(第2页)
第六百一十三章 你醒啦(第2页)
对方直逼碑林,领头者冷声道:“最后一刻,你们还可选择撤去此碑,回归沉默。否则,我们将以‘清魂阵’将其彻底封印,连同你们的记忆一起抹去。”
陈砚踏前一步:“你们口口声声说为了太平,可曾问过那些枉死者,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太平?是尸骨无名,还是后代跪拜仇人牌位?”
“情感滋生纷争,记忆引发仇恨。”那人漠然回应,“唯有遗忘,才是终极和平。”
“那你们为何还要记得自己是谁?”柳念安冷笑,“若真求忘,何必披甲执刃而来?不如投胎转世,做个无知婴儿!”
对方微微一顿,似被刺中。
就在此刻,苏渺抬手,残笛吹响第一音。紧接着,柳念安击鼓,净尘诵咒,陈砚取出银笛,与胸前玉笛并列,第九音再度响起。
四野回应。
不只是人声,更是天地共鸣。
从山间,从河底,从古树根须之间,千万缕幽光升起,汇聚成河。那是八千亡魂的意志,也是百万生者的共情。光芒交织,在空中凝成巨大人影??赫然是林昭的模样,衣袂飘飞,目光如炬。
守寂人纷纷后退。
“这……不可能!”首领嘶吼,“死人怎可显形?!”
“不是显形。”陈砚平静道,“是你们一直不肯承认的事终于站起来了??**正义或许迟到,但从不缺席;记忆或许被埋,但从不死去。**”
林昭虚影缓缓抬手,指向黑幡。刹那间,火焰自幡角燃起,迅速蔓延。那火非红非蓝,而是纯净的白,烧过之处,黑气尽数消散。守寂人手中的兵器寸寸断裂,面具崩裂,露出一张张苍老而痛苦的脸??他们中许多人,竟是当年被迫加入忘川司的老兵、史官、狱卒。
“我们……也是被骗的……”一人跪下,颤抖着摘下面具,“他们说只要删去名字,就能换来安宁……可我们夜里总是梦见他们在哭……”
陈砚走上前,扶起那人:“现在还不晚。你们可以成为新的执灯使。”
雨,不知何时停了。
东方微亮,晨曦洒落碑林。每一块石碑都泛着温润光泽,仿佛吸饱了星光。那道地裂已被青苔悄然覆盖,如同大地自行愈合了伤口。
数日后,朝廷再次下诏:废除“忘川”相关一切禁令,开放历代秘档供民间查阅;设立“铭名书院”,培养独立史官;凡隐瞒或篡改历史者,无论官职高低,一律革职查办。
更令人震动的是,前宰相之孙主动交出家族私藏的《删史手札》,其中详细记录了三十年间如何系统性抹去异己姓名的过程。执灯使据此追查,陆续找回近两千个被彻底湮灭的名字,并一一补录入正名碑。
这一年清明,铭名节空前盛大。全国上下,家家门前挂灯,户户焚香祭祖。皇帝亲赴皇陵,立誓:“朕愿为天下首忏,自此不敢再掩一字。”
皇后则带来一幅新绘的长卷??画中,林昭立于风雨朝堂,手持奏折,身后跟着无数模糊身影,皆仰面望天,似在等待阳光穿透乌云。
她在画旁题字:“**她不曾低头,故我不敢闭眼。**”
岁月流转,十年如一日。
执灯使已成为一种信仰,而非组织。他们行走于乡野,记录口述历史;潜入旧宅,抢救濒毁文献;甚至远赴海外,寻回流失的族谱残卷。每一份材料都被妥善保存于昭明馆地下九层,那里已建成一座庞大的“记忆之库”,按地域、年代、事件分类,可供任何人查阅。
陈砚年岁渐高,两鬓染霜,但仍每日伏案书写。他编纂的《重光纪》即将完成,这部巨著不仅收录被删之名,更剖析权力如何运作于记忆之上,警示后人:“**最可怕的暴政,不是杀人,而是让人忘记谁杀了人。**”
某个春夜,孙儿跑进书房,兴奋地说:“爷爷!学校今天教了你的故事!老师说,你是点亮第一盏灯的人!”
陈砚笑着摸摸他的头:“不,孩子,第一盏灯,是你曾祖母点的。我只是……没让它熄灭。”
次日,他独自登上皇陵最高处。春风拂面,忆莲盛开如海。他取出银笛,轻轻吹响第九音。远处村落,有孩童听见,竟也哼起《忆昭辞》。歌声随风飘荡,越传越远。
他知道,这场战争从未结束,也不会真正结束。只要人类还拥有权力与恐惧,就会有人试图抹去过去。但他也明白,只要还有一个母亲愿意对孩子说“从前有个女子叫林昭”,只要还有一个学生敢于质问课本里的空白,光就会一代代传下去。
黄昏时分,一只白鹤自南方飞来,落在碑前。它衔着一片枯叶,轻轻放下。叶上墨迹依稀可见:
>**“名字回来了,我也该走了。”**
陈砚认得这笔迹。
是裴仲言。
这位曾持刀而来、最终跪读父名的兵部侍郎,在晚年辞官归隐,游历四方,致力于搜集冤案证据。三个月前,他在边陲小镇病逝,临终前留下遗言:“请将我葬于无名冢旁,让我为他们守夜。”
陈砚捡起叶子,放入怀中,抬头望天。
暮色四合,星辰初现。名河依旧横贯夜空,比以往更加明亮。
他轻声说道:“你们看,风起了。”
风穿过松林,吹动长幡,拂过每一座石碑。
那些名字,在月下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