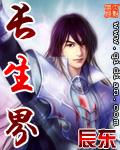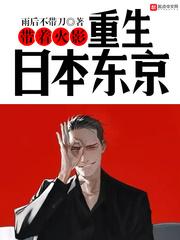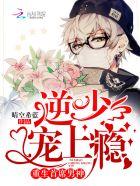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大明第一国舅 > 第688章 彻彻底底的查(第2页)
第688章 彻彻底底的查(第2页)
回到驿馆,他立即召集赵小勇与两名心腹密议。经彻夜梳理,终于理出一条线索:所有赈灾钱粮的转运记录,均由西安府通判王?经手,而此人三年前曾因贪墨被贬,后不知何故又被起复,且与李善长府中管家往来密切。
“查他。”马寻果断下令。
当夜,赵小勇带人潜入王?宅邸,在其书房暗格中搜出一本密账,记载着自洪武八年至今,陕西省各地虚报灾情、套取钱粮的详细数目,以及各环节分赃比例。最令人震惊的是,账本末页赫然写着一行小字:“每岁所得,三成归中枢,五成归藩邸,余者地方自留。”
“中枢……是李善长?”赵小勇颤声问。
马寻盯着那行字,久久不语。三成归中枢,意味着这笔黑钱有一部分流入了李善长手中;而五成归藩邸,难道是指诸王?尤其是镇守一方的秦王?
他猛然想起朱桢昨夜那番话??悲愤、无奈、隐忍。或许,朱桢早已知晓内情,却无力改变。毕竟,若没有上面默许,一个小小的布政使怎敢如此大胆?
正思索间,忽闻门外喧哗。一名家丁模样的人跌撞闯入,满脸血污:“马大人救命!我家老爷……王通判,刚被人吊死在后院槐树上!”
马寻霍然起身。
赶至王宅,只见王?尸首悬于树梢,脖颈勒痕深紫,嘴角溢血,双手被反绑,脚下散落着几页残纸。捡起一看,竟是那份密账的复印件!
“有人灭口。”马寻咬牙切齿,“而且就在我们动手之后。”
他环顾四周,院墙完好,门户未破,凶手显然是熟门熟路,甚至可能就在府中任职之人。更可怕的是,对方能在短短半个时辰内得知搜查行动并实施杀人,说明驿馆之中已有奸细。
回程路上,马寻沉默不语。他知道,自己已踏入一张无形巨网,每走一步,都有性命之忧。但退,已无路可退。
第三日黎明,他再次求见秦王。
朱桢已在偏殿等候,神色疲惫。
“查到了什么?”他问。
马寻呈上密账副本,一字一句道:“渭南无灾,灾情系伪造。陕西上下官吏勾结,虚报灾户三万余,骗取朝廷粮一万八千石、铜钱千余贯。其中,三成贿送李善长府,五成流入秦王府库房,余者由地方瓜分。”
殿内死寂。
良久,朱桢缓缓闭眼,声音沙哑:“果然如此。”
“殿下早知?”马寻震惊。
朱桢苦笑:“我若不知,怎会容他们在眼皮底下胡作非为?可你知道我为何装聋作哑?因为我父皇说过??‘诸王镇边,财赋自筹’。这句话听着风光,实则是逼我们自谋生路。没有朝廷俸禄,没有额外拨款,边防要养兵,王府要运转,靠什么?靠的就是这些‘灾情’!”
马寻如遭雷击。
原来如此。皇帝一面削藩,一面又默许诸王通过虚报灾情获取资金,既维持表面稳定,又避免直接授人以柄。这是一种极其阴险的政治平衡术。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朱桢突然睁眼,直视马寻,“揭发我?还是替我遮掩?”
马寻沉默片刻,缓缓跪下:“下官只求一件事??将居养院改为实济之所,收容真正流民;将历年贪墨之财,尽数返还百姓。其余……任凭殿下处置。”
朱桢怔住,随即仰天长叹:“汤和有你这样的外甥,真是大明之福。”
三日后,朝廷诏书下达:渭南县令因“失察之罪”革职查办,王?“畏罪自尽”,其余涉案人员暂不追究。同时,敕令陕西各地整修居养院,增设粥棚,接纳流民。秦王朱桢上表谢罪,自愿削减岁禄三成,以补国用。
表面上,风波平息。
但马寻知道,这只是冰山一角。那本密账已被送往应天府,交至汤和手中。而李善长那边,也开始动作频频??先是弹劾冯胜“擅调兵马”,继而提议整顿东厂,削弱厂卫权力。
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一个月后,马寻启程返京。临行前夜,朱桢独自来访。
“你走之后,我会烧了那座居养院。”他说,“烧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
马寻点头:“该烧。”
朱桢看着他,忽然低声问:“如果有一天,我也成了必须被烧掉的东西,你会动手吗?”
马寻沉默良久,答:“若殿下为天下苍生计,我愿护你周全;若殿下为一己私欲害万民,纵是亲舅之子,我也绝不手软。”
朱桢笑了,拍拍他肩:“好小子,不愧是我大明第一国舅。”
风起渭水,云涌长安。这场关于灾情的博弈,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