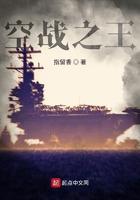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重回1982小渔村 > 第1767章 承包(第1页)
第1767章 承包(第1页)
叶耀东看了一下手表,还有半小时左右下班,开始交接,看他们应该也无心上班的样子,也不勉强。
毕竟都还小,孩子心性,刚得了10块钱,估计已经高兴的坐不住了,反正也不指望他们干多少活。
“你们要。。。
海风卷着细雨扑在脸上,阿禾站在蜂巢塔外的石阶上,望着孩子们手中摇曳的灯火。那些纸灯笼歪歪扭扭地升空,像一群初学飞翔的萤火虫,在夜幕中划出颤抖的光痕。铜铃叮当轻响,一声接一声,与远处海浪拍岸的节奏悄然应和。
她低头看着掌心那张湿漉漉又烘干的纸条,背面那句“下一个迷路的人,已在路上”依旧清晰如刻。不是预言,是召唤。血脉的记忆从未真正断绝,它只是沉入海底,等待一次共鸣,一次回响。
李院长的电话再度打来时,已是凌晨两点。
“男孩今早醒了,第一次开口说话。”她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震颤,“他说了三个字??‘归名镇’。”
阿禾握紧手机,指节发白。那个被救起后改名换姓、辗转多地的婴儿,竟在昏迷三个月后,凭着某种深埋于骨血中的记忆,说出了故乡的名字。
“他还画了东西吗?”她问。
“画了一艘船,船头站着两个人,一个大人抱着孩子。他在船尾添了个小铃铛,还用红笔圈起来。”李院长顿了顿,“阿禾,这孩子……他右手指尖缺了半截小指的事,我们没对外公布过。”
阿禾闭上眼。这不是巧合。这是轮回般的重演,是命运以最沉默的方式,把未完的故事递到了下一棒手中。
她挂了电话,转身走进蜂巢塔。主控室的屏幕还在闪烁,全球共感网络的数据流如星河般滚动。东海沿岸的情绪波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呈扩散趋势。福建霞浦的一位老渔民昨夜录下一段音频:深夜渔船停泊港湾,收音机突然自动开启,播放的竟是五十年代归名镇广播站特有的《月娘光光》前奏曲调,音质陈旧,却真实存在。
更诡异的是,浙江温岭一家临海民宿的监控显示,凌晨三点十七分,所有住客的房门把手同时轻微转动,仿佛有人逐一探查。而屋内无人醒来,唯有床头摆放的金属物件??钥匙、发卡、汤匙??齐齐发出微弱共振,频率正是118。3Hz。
阿禾调出蜂巢塔的能量分布图,发现地下第七层的“记忆锚点池”正在自发充能。那是她当初为保存上海福利院那次集体共鸣所设的封闭系统,理论上不应有任何外部输入。可此刻,能量曲线正以每小时6。7%的速度攀升,来源不明。
她穿上共振服,启动低频探测模式,将意识接入锚点池。刚一连接,耳边便响起孩童的哼唱声,稚嫩、断续,却异常清晰:
>“月娘光光,照我眠床,
>阿爸出海,莫忘归航……”
这不是录音。这是实时传入的意识片段。
画面浮现:一间昏暗的小屋,墙上挂着褪色的渔网,桌上摆着半碗冷粥。一个瘦弱男孩蜷缩在角落,手里攥着一支铅笔,在纸上疯狂涂画。他画的是一座灯塔,塔顶悬着一枚铜铃,铃下站着许多人,手牵着手,围成一圈。
忽然,窗外传来脚步声。很轻,像是赤脚踩在泥地上。男孩猛地抬头,眼神惊恐又期待。
门开了。
门口站着一个穿蓑衣的男人,脸藏在阴影里,只有一只右手伸出??指尖缺了半截小指。
男孩张嘴想喊,却发不出声音。
就在这一刻,阿禾感到脑中一阵剧痛,仿佛有无数根针刺入神经。她强行维持连接,伸手“触”向那个男人的身影。指尖相碰的刹那,一股庞大而混乱的记忆洪流汹涌灌入:
**1998年夏末,台风“森姆”来袭。**
一艘从马祖驶往福州的客轮在闽江口外海失联。船上共有二十三人,其中包括一对携婴返陆探亲的夫妻??周家堂弟夫妇,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周念舟(原名周承远)。
风暴中,父亲将儿子塞进救生衣,绑在浮木上推离沉船。他自己回头去拉妻子,却被巨浪卷走。三天后,男孩在浙江象山海滩被渔民发现,高烧昏迷,右手小指被礁石割断。父母遗体始终未寻获。
他被送至宁波福利院,因创伤失语,辗转六家机构,最终落户上海。没人知道他的身世,档案上只有“无名男童”四字。直到三个月前,他在梦中惊醒,反复念叨“灯塔”、“铃声”、“爸爸没回来”,院方才紧急联系李院长。
而那一晚,当他听见《月娘光光》的旋律时,沉睡的血脉终于苏醒。
阿禾猛然退出连接,跌坐在地,冷汗涔涔。她终于明白为何这个孩子会与周海生如此相似??他是周海生的侄孙,也是“念舟”之名的真正继承者。当年周海生未能归航,他的执念化作信号穿越时空;如今,这份执念找到了新的载体,一个新的“念舟”,再次站在了命运的起点。
她颤抖着打开族谱扫描件,在“周承远”三字旁标注红圈,写下一行字:
>**念舟非一人,乃一代代未归之人之名。**
窗外,雨势渐歇。东方天际泛起鱼肚白,蜂巢塔顶的铜铃忽然轻轻一震,仿佛感应到了什么。
阿禾站起身,拨通李院长电话:“请安排最快的方式,把他送来归名镇。不要告诉他目的地,就说是‘去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