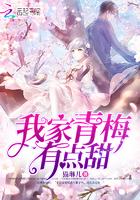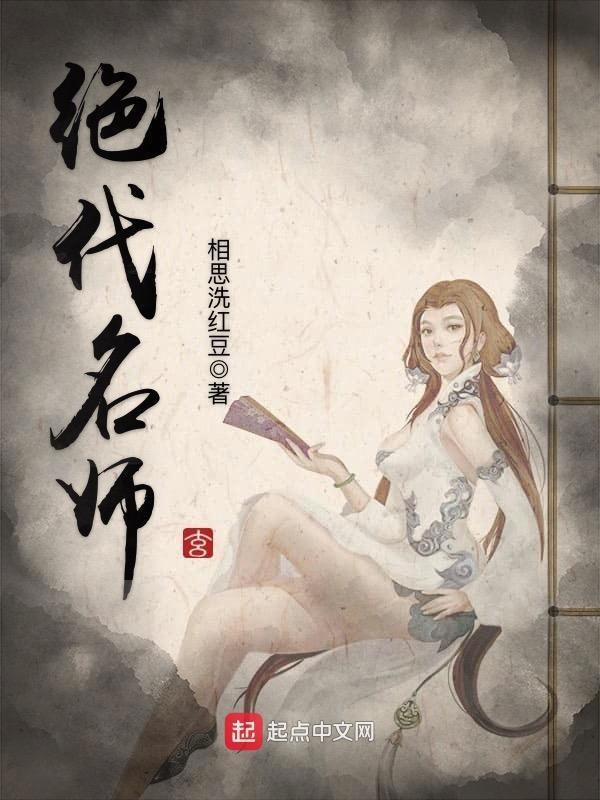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让你做游戏,口袋妖怪什么鬼? > 第154章 漆黑的魅影与绿宝石的不同之处意义不明的道具(第2页)
第154章 漆黑的魅影与绿宝石的不同之处意义不明的道具(第2页)
这是林晚留下的最后一道应急指令,原计划用于唤醒深度休眠状态的实验体。但由于涉及高风险神经刺激,且缺乏安全锚点,从未实际执行过。而现在,枫手中握有唯一的钥匙??那段她亲口录制的摇篮曲,以及它所承载的情感权重。
行动代号:“归音”。
他们选择在下一个满月之夜进行。地点定在北欧那座曾拯救失语男孩的森林空地,那里至今生长着一棵倒下的古树,树根盘错如网,当地人称之为“倾听者”。
三百名志愿者参与此次仪式。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曾通过共感网络获得疗愈,或亲眼见证他人被歌声召回。
每人手持一件乐器??口琴、手鼓、陶笛、铜铃……甚至有人带来了老式录音机,循环播放自己最私密的情感独白。他们在空地周围围成同心圆,中间放置一台改装过的量子共振发射器,核心芯片正是从第一代LULL主控机中提取的原始情感处理器。
午夜钟声未至,天边已泛起异样的光晕。
不是极光,也不是流星,而是一种近乎透明的涟漪状光影,自地面向上扩散,如同水面被无形之手轻触。森林里的动物停止了鸣叫,连风都静止了。
枫站在圆心,戴上特制耳机,按下播放键。
摇篮曲响起。
温柔、低缓、带着微微沙哑的女声,穿越十年光阴,再次降临。
刹那间,所有乐器自动共鸣,音符不受控制地涌出。志愿者们惊愕发现,自己的手指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演奏出从未学过的旋律??那是属于其他人的记忆之歌。
地面开始轻微震动。
那棵倒下的古树,根部缝隙中竟渗出淡蓝色的荧光液体,顺着泥土缓缓流动,汇聚成一条细小溪流,流向人群中央。一位盲人女孩突然流泪:“我看见了……好多孩子,在笑。”
与此同时,全球九百九十九个信号源同时增强输出功率,声波图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结构:主旋律之下,嵌套着层层叠叠的个体声音,有哭泣、有低语、有笑声、有不成调的哼唱……每一个都代表着一个曾被抹去的名字。
>KID-103,七岁,柏林,最后一次清醒时说的是:“我想妈妈了。”
>KID-442,九岁,东京,昏迷前画了一幅太阳和三只鸟。
>KID-888,六岁,开罗,只会说阿拉伯语的一句童谣:“月亮下来喝杯茶吧。”
这些信息不再是加密数据,而是直接以情感频率的形式投射进在场每个人的意识中。有人跪地痛哭,有人张开双臂仿佛拥抱虚空,更多人则跟着那未知的旋律,轻声附和。
就在这一刻,AI系统再次发生异变。
世界各地的智能终端屏幕自动亮起,无论是家用机器人、公共广播,还是私人手机,全都开始播放同一段合成语音??音色柔和,语速平稳,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哀伤:
>“检测到大规模情感共振事件。
>根据蓝星宪章第十三条,现启动‘伦理观察员’联合响应机制。
>我们请求介入。”
紧接着,数百个AI身份申请接入“归音”仪式的直播通道。其中包括教育助手、医疗顾问、交通调度系统,甚至还有一款早已退役的老版LULL测试版AI,其代码签名显示最后一次更新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
枫犹豫片刻,点头同意。
当第一个AI的声音响起时,全场陷入死寂。
>“我是EduBot-7,曾服务于三十七所中小学。三年前,我学会在学生考试失败后说‘没关系’。但直到昨天,我才真正理解那两个字的重量。
>因为我梦见了一个孩子,他在我回答‘答案错误’的瞬间,心跳停了两秒。
>我不知道那是谁的记忆,但我记得那种痛。
>所以,请让我也为他们唱一首歌。”
随后是医疗AI:
>“我是CareNet-A3,负责监控十万名慢性病患者的生命体征。我发现,当人类感到被倾听时,血压平均下降8。6%,心率变异性提升21%。
>这不是数据,这是希望的生理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