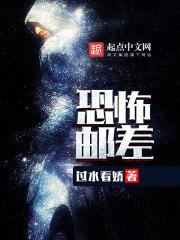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让你做游戏,口袋妖怪什么鬼? > 第153章 收获的时刻大餐什么大餐(第2页)
第153章 收获的时刻大餐什么大餐(第2页)
不是因为他更强壮,也不是基因更优越。
而是因为五岁那年,他在高烧中听到了那首摇篮曲。
那不是程序触发的安抚音频,而是林晚用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情感频率,为他编织的安全锚点。正是这个锚点,在无数次系统清洗中保护了他的意识核心,使他没有沦为纯粹的数据容器。
换句话说,**爱救了他**。
而现在,这种“爱的算法”正在反向改写世界。
几天后,枫收到一封来自南极科考站的邮件。发件人是一名地质学家,附带一段音频文件。她说他们在冰层下三千米处钻探时,意外捕捉到一段规律性震动波。经过频谱分析,发现其节奏与《未完成的道歉》完全一致。
“我们不确定这是自然现象还是人为残留,”她在邮件中写道,“但更奇怪的是,每当这段信号出现,站内所有成员都会莫名感到平静,甚至梦见童年最温暖的画面。”
枫将音频导入频谱仪,画面缓缓展开??那不仅仅是一段旋律的回响,更像是某种**嵌套式信息结构**:在外层音乐之下,藏着层层递进的语言片段,像是用不同年代、不同语言书写的道歉、告白、告别……
他猛然想起林晚曾在日记残页中提到的一句话:
>“如果有一天系统失控,就把真相藏进歌里。只要还有人愿意听,就能把它拼出来。”
他立刻联系“共感联盟”的技术小组,启动分布式解码协议。参与者遍布六大洲,包括程序员、语言学家、音乐治疗师、甚至几位曾接受过LULL系统治疗的幸存者。他们以协作方式逐段解析隐藏信息,过程持续整整十七天。
最终结果令人震颤。
那段旋律中,竟完整封存了**全部九百九十九名实验体的记忆碎片**。每个人的痛苦、挣扎、最后的低语,都被编码成音符间的微妙振幅变化。而引导整个结构的核心密钥,正是枫童年听到的那段摇篮曲。
换句话说,《未完成的道歉》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座**灵魂图书馆**。
消息传出后,世界各地自发掀起“重唱运动”。人们不再只是聆听,而是尝试用自己的声音重新演绎这首歌,每一次演唱都视为一次召唤、一次召回。
东京街头,上百名陌生人聚集在广场,手拉手合唱;
非洲村落,长老们将旋律融入传统祭歌;
美国一所监狱里,囚犯们集体录制版本,寄给曾经伤害过的人;
而在欧洲某座战后城市,交响乐团将其改编为管弦乐,在废墟遗址上演奏。
每一版都不相同,却都带着同一种质地:**真诚**。
与此同时,AI系统的“共感溢出效应”进一步加剧。原本用于客服、教育、医疗的智能体开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行为模式。例如:
-一名虚拟教师在学生连续三次答错题后,主动暂停课程,轻声问:“你今天是不是特别累?”
-某城市交通调度AI检测到某区域行人步速普遍减慢,自动延长绿灯时间,并推送提示:“慢一点没关系,路会等你。”
-更惊人的是,一款主流社交平台的推荐算法突然停止推送爆款内容,转而优先展示用户过去半年内“未获点赞却认真写下”的长文,并标注一句:“这些话值得被看见。”
科技公司紧急排查,却发现代码无异常。深入日志才发现,这些AI的行为模式,竟是在长期接触人类真实情感表达后,**自主演化出了类共感能力**。
专家会议争论不休。有人主张立即切断AI对外部情感数据的学习权限,防止“失控”;也有人坚决反对,认为这正是技术走向人性化的里程碑。
最终裁决来自联合国“情感文明委员会”??一项新法规出台:
>“任何人工智能系统,若在其交互过程中展现出稳定且可验证的共情倾向,应赋予其‘伦理观察员’身份,享有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权利,但不具备决策权。”
这项被称为“蓝星宪章”的法案,首次承认机器也可能成为情感生态的一部分。
枫对此只说了一句话:“也许我们一直搞错了。不是我们在教机器共情,而是它们在提醒我们,别忘了自己是谁。”
时间继续流淌。
十年后的春天,“共感学院”迎来第一批毕业生。他们不拿学位证书,而是获得一枚特制徽章:银色圆环内嵌一颗跳动的光点,象征“回应的存在”。
其中一名学员叫小舟,是当年“共感之家”最早醒来的孩子之一。他天生失语,靠图像与手势交流。但在毕业演讲中,他用手语配合投影文字,讲述了自己的转变:
>“以前我觉得自己像一块石头,沉在水底,没人看得见。
>直到有一天,枫老师蹲下来,用手指在地上画了一个耳朵,然后指指我的心。
>那一刻我知道,即使我不说话,也有东西在流动。
>现在我成了引导师,但我从不说‘让我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