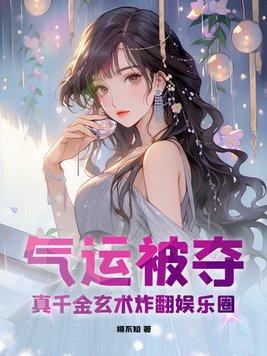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蜀汉之庄稼汉 > 第1457章 疯了(第3页)
第1457章 疯了(第3页)
冯大司马静听良久,最终开口:“传我命令:第一,撤销对流民的一切收费项目,所有农具免费发放,由国库承担;第二,派遣五百名太学生下乡,协助教导耕种技术,宣扬朝廷仁政;第三,设立‘举报重赏制’,凡揭发兴农会成员者,赏绢十匹、田二十亩。”
众人愕然。
有人忍不住问:“如此宽仁,岂非纵容奸邪?”
冯大司马淡淡道:“真正的敌人不是这群被蛊惑的百姓,而是躲在背后的操盘手。我们要做的,不是用刀逼他们屈服,而是用恩德让他们觉醒。当一个人吃饱了饭,有了地,还能读书明理,他还会愿意为一句空洞的‘复土’去拼命吗?”
三日后,政策全面推行。
不出半月,流民营中风气大变。原本半信半疑的百姓发现,官府不仅不收钱,反而派老师教他们识字算账,教妇人纺织养蚕,甚至开设“子弟学堂”,允许孩童免费入学。
而那些曾加入兴农会的人,开始陆续退出。有人撕毁会籍,有人主动举报同伙。短短二十天,兴农会网络崩塌过半。
藏身暗处的黑衣人怒不可遏,下令提前起事。
四月初八夜,三更天,?县东营突然火光冲天。百余手持棍棒刀斧的流民冲向粮仓,高呼“还我家乡”“驱逐奸官”。守营官兵猝不及防,一度被逼退。
眼看局势失控,忽听号角连鸣,四面八方亮起无数火把。五千羽林军自隐蔽营地杀出,将暴动者团团围住。与此同时,广播车缓缓驶入营区,喇叭中传出冯大司马亲录的声音:
>“尔等皆我骨肉同胞,自北而来,受尽苦难。我开仓赈济,授田安家,只为让你们活下去,活得有尊严。若有不满,可诉诸官府,可上书言事。为何要听信谗言,自相残杀?今夜之事,为首者死,胁从者恕。愿悔改者,仍可领种耕田,安居乐业。”
声如洪钟,传遍四方。
许多参与暴动的流民听到这话,当场跪地痛哭。带队的几名“教头”见大势已去,拔刀欲搏,旋即被弩箭射杀。
黎明时分,大火熄灭,秩序恢复。
冯大司马亲临现场,查看伤亡情况。当他看到一名十六七岁的少年蜷缩在尸堆旁瑟瑟发抖时,蹲下身问道:“你为何参与?”
少年抽泣道:“他们说……只要烧了粮仓,就能拿到路费回家……我想看看娘坟上的草,是不是长得比去年高了……”
冯大司马久久无言。
良久,他脱下外袍披在少年身上,轻声道:“跟我走吧。我带你回长安,读书识字,然后……我派你去做官,去管那些像你一样的人,别再让他们被骗。”
少年泪流满面,重重磕头。
此事传开后,民心彻底归附。连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吴国士人也纷纷议论:“冯某人治国,不在兵强马壮,而在得人心。如此人物,岂是司马仲达可比?”
而在长安深处,羊祜终于收到一封密信,拆开只见八个字:
>“槐叶已枯,君宜早决。”
他坐在灯下,盯着那片干瘪的叶子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清晨,他主动走入校事府,交出一枚刻有“魏武旧部”字样的玉佩,坦承自己半年前曾与叔父通信,知晓部分阴谋,但始终未予回应。
“我不是忠臣,也不是逆贼。”他说,“我只是……不想再看见战争。”
冯大司马得知后,亲自前往狱中探望。
两人相对无言,许久,冯大司马才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留你在太学吗?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想起我们小时候说过的话。”
羊祜抬头看他,眼中含泪:“我记得。你说,真正的英雄,不是砍下最多人头的那个,而是能让最多人活下去的那个。”
冯大司马点头:“现在,你愿意帮我一起种庄稼了吗?”
羊祜缓缓跪下,叩首至地。
风暴渐息,春耕正忙。
长安郊外,万亩新田泛起绿波。农夫扶犁,孩童追蝶,老妪倚门唤孙归食。
冯大司马立于高坡之上,望着这片复苏的土地,轻叹一声:“乱世用重典,治世贵养民。你们想乱?好啊。我就用这一茬茬的庄稼,把你们的仇恨,全都埋进土里。”
风过原野,麦苗摇曳,如海浪般起伏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