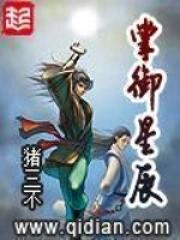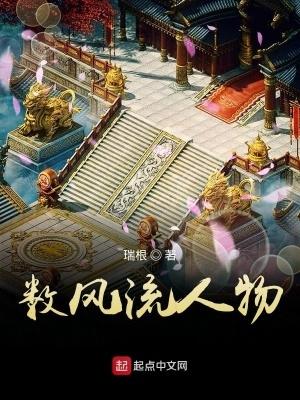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蜀汉之庄稼汉 > 第1457章 疯了(第1页)
第1457章 疯了(第1页)
建业城的皇宫深处,丹炉的燥热与深宫的阴冷气息交织。
孙权斜倚在御榻上,眼窝深陷,瞳孔深处却燃烧着丹药带来的虚妄之火,仿佛瞥见了蓬莱仙岛的幻影,又仿佛有怒火在燃烧。
常年的修仙,再加上磕致幻。。。
夜色如墨,长安城外的渭水河畔却灯火点点。数千流民正在官府役吏的引导下,分批渡河入营。临时搭建的草棚连绵数里,锅灶炊烟袅袅升起,孩童啼哭、老者咳嗽声此起彼伏,却无人喧哗??皆因每十户便有一名“农正”值守,手持黄册登记姓名籍贯,发放米粮与种子。
这是冯大司马推行“安流策”的第三十七日。
自下令开仓赈济以来,已有五万六千余名北人流民归附季汉,尽数安置于渭南、?县一带,按“五户一伍、十伍一里”编组,授田三十亩,三年免赋,官给耕牛、铁犁、麦种,并派屯田都尉督劝农事。更有医官巡诊施药,防瘟疫滋生。百姓初来时面黄肌瘦、衣不蔽体,如今已有不少人面色渐润,开始自发修缮屋舍,垦荒整地。
一名年约四旬的妇人抱着幼子站在领种处前,颤抖着接过两袋冬小麦种,眼泪簌簌落下:“三年……真能三年不缴税?”
身旁年轻小吏点头微笑:“夫人放心,君侯亲笔诏令已颁至各县,若有官吏私自加征,可赴长安台前击鼓鸣冤。”
那妇人跪地叩首,哽咽难言。她身后,百余人默默跪倒,齐声道:“谢大司马活命之恩!”
这一幕,被藏身于十里外山岗上的两名黑衣人尽收眼底。
“看来他是真想把这些流民变成良民。”一人低语,声音沙哑,“种地、纳粮、生子,一代之后,谁还记得故乡在青州?谁还会想着复仇?”
另一人冷笑:“所以他才可怕。别人用刀剑杀人,他用土地和粮食收心。你以为这些人感激的是粮食?不,他们感激的是‘希望’。而有了希望的人,最不愿再乱。”
先前者沉默片刻,忽问:“你说……我们还能阻止吗?”
后者缓缓抽出腰间短匕,在掌心划出一道血痕:“只要血还在流,仇恨就不会断。明日午时,兴农会第一批‘教头’将潜入?县,在流民营中传《复土书》,讲河东惨案,播反汉火种。只要三个人里有一个心动,火就能烧起来。”
***
与此同时,荆州江陵。
王?立于战船船头,披甲佩剑,目光如鹰隼扫视江面。身后三千飞骑营已换轻舟快艇,隐蔽于芦苇荡中,随时可顺流东下直扑建业。
一名校尉疾步上前:“将军,刚接到密报:吴国丹阳郡昨夜发生暴乱,数百北人流民围攻县衙,砸仓夺粮,守令险些被杀。孙权震怒,已命陆凯率兵五千前往镇压,并下令沿江诸郡凡有北人聚众十人以上者,格杀勿论。”
王?眉头微皱:“当真是流民作乱?还是有人煽动?”
“细作回报,事发前夜,曾有一蒙面人潜入流民营,散发写有‘季汉拒我,吴人欺我,不如自立’八字的布条。且参与者多为青壮男子,行动有序,非饥民所能为之。”
王?冷哼一声:“果然来了。”他转身对亲兵道:“立刻传信长安,请君侯定夺。另遣八百里加急送书荆州刺史,命其封锁长江上下游,所有船只不得擅离码头,违者以通敌论处。”
话音未落,江风骤急,乌云蔽月。
忽然,下游传来号角三响??是约定的警讯。
王?猛然抬头,只见远处江心浮出十余艘无灯小舟,形似渔艇,却行速极快,逆流而上,竟似不受水流影响。舟上之人皆裹黑巾,背负长匣。
“拦江弩阵准备!”王?厉声下令。
刹那间,两岸弓弩手齐出,数十具床子弩对准江心。一声梆子响,箭雨倾泻而下,江面激起层层白浪。三艘小舟当场被钉穿沉没,其余则迅速分散,借雾遁逃。
搜捕半个时辰后,仅擒获两人,皆服毒自尽。但从一艘沉船上打捞出的木匣中,却发现数十枚刻有“魏故振威将军印”的铜牌,以及一封未及送出的密信:
>“羊氏子已在长安埋首待发,只等兖州举事,便可内外呼应。冯某人若知其妻族暗通旧魏遗党,不知当作何想?”
王?看完信笺,脸色铁青。他立即命人将信件火漆封缄,亲自誊抄三份:一份八百里加急送往长安,一份密送成都丞相府,最后一份,则锁入私匣,藏于舱底。
他知道,这已不只是边患之争,而是人心之战。
***
长安,冯府。
冯大司马正在校阅新编的《流民户籍总册》,忽闻门外脚步急促。羊徽瑜推门而入,面色罕见地凝重。
“夫君……我刚从族中elder那里得知,我叔父半月前曾秘密接见一名自称来自兖州的客商,那人走后,家中便少了二十口精壮奴仆,至今未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