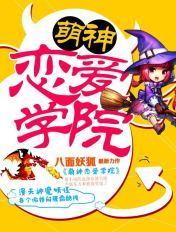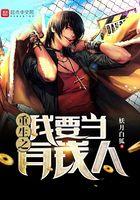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柯南:我真觉得米花町是天堂 > 第421章(第3页)
第421章(第3页)
“你……为什么会来找我?”
“因为你说了话。”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宁愿痛苦也不愿开口。而你选择了说出最沉重的秘密。这就说明,你心里还有希望。”
她怔怔地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光亮。
当天傍晚,在当地社工协助下,女人被送往专业心理机构接受长期治疗。临别时,她递给纪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画着两个牵手的小人,头顶写着:“对不起,弟弟。”
纪一带着这张画回到了东京。
一周后,他收到一封邮件,署名是那位女人的主治医生:
>“她已经开始书写回忆录。昨天,她第一次主动提起弟弟的名字??健太。
>她说,想为他录一首歌,作为迟到的生日礼物。
>我们会把录音上传至声音档案馆。
>谢谢你,让她终于敢说出这个名字。”
纪一读完,久久不能言语。
他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更多开始的预兆。
又过了几天,国际心理健康峰会邀请他作为特邀嘉宾发表演讲。主办方原本只想让他谈谈《归音》的社会影响,但他提交的讲题却是:
>《论声音的权利:当共情成为基础设施》
演讲当天,礼堂座无虚席。各国学者、政策制定者、科技公司代表齐聚一堂。聚光灯打在他身上,纪一站上讲台,没有使用PPT,也没有数据图表,只带来一台老式录音机。
“各位,请先听一段声音。”他说。
按下播放键。
先是雨声,淅淅沥沥;然后是一个小女孩颤抖的声音:
“健太……对不起……姐姐没能保护好你……但我会一直记得你最爱吃的草莓牛奶……每年春天,我都放在你照片前……你要乖乖长大啊……”
全场寂静。
纪一关掉录音,环视众人。
“这不是艺术,也不是实验。这是一个真实的人,在经历了十六年沉默后,第一次向世界道歉,也是第一次尝试原谅自己。”
他停顿片刻,继续说道:
“我们常以为,科技进步是为了让人更高效、更快乐、更长寿。但我们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人最深的痛苦,从来不是孤独本身,而是明明身处人群,却无法传达内心的重量。
所以,当我母亲创造《归音》时,她不是在发明一种音乐疗法,而是在挑战一个根本问题:
**如果语言会撒谎,文字会被篡改,图像可以修饰,那么,还有什么能真正承载一个人的真实?**
答案是声音。
因为声音无法完全伪装。
一个颤抖的尾音,一次呼吸的迟疑,一段哽咽中的停顿??这些细微之处,藏着灵魂最原始的密码。
今天我们讨论AI、脑机接口、情感计算……但我们必须记住:
技术不该教会机器如何模仿人类的情感,
而应帮助人类重新学会彼此倾听。
《归音》不是终点,它只是一个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