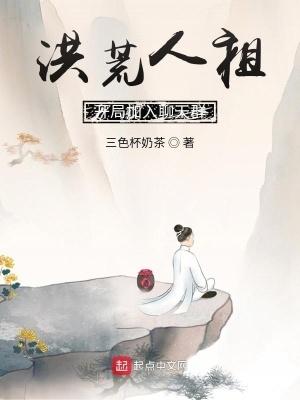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斗罗:龙王之太极玄真 > 第二百四十一章 岳父大人夸我啦冲徒逆师绯红色不眠之夜4K(第1页)
第二百四十一章 岳父大人夸我啦冲徒逆师绯红色不眠之夜4K(第1页)
遥远太空。
一团光球看似缓慢,实则以近乎空间跳跃般的速度前进。
光球内彩光氤氲,仙云渺渺,正是受到时空乱流落入黑洞,漂流宇宙的神界。
神界中枢之内,十二神王轮流主持此方世界,控制光球。。。
风在回声号的外壳上划出细微的震颤,不是来自宇宙风暴,而是某种更深层的共振。林小愿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竹笛裂纹,那道从第七节一直延伸到吹口的伤痕,如今已不再渗血??那是七年前她在灰语星第一次试图吹响“真音”时,笛子与心脉共鸣崩裂所致。可每当她靠近一颗尚未觉醒的星球,那裂口便会微微发烫,像是提醒她:有些伤口,本就是通往声音的通道。
航程第三日,赤砂星的轮廓在雷达上浮现。这颗星球表面覆盖着无边的红沙,大气稀薄,氧气含量仅维持生命最低阈值。三百年前,一场语言瘟疫席卷全境,九成人口因言语失控被判定为“情绪污染源”,遭集体静默处理。自那以后,赤砂人以手势、光影、触碰交流,语言成为禁忌,连婴儿啼哭都被定义为“初级声波危害”。
林小愿穿上了最朴素的防护服,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或翻译设备。她只带了两样东西:竹笛,和一张手绘的地图??那是启鸣号共生意志根据古老星图推演而出的“沉默者行迹”,标注了十二个曾发生大规模语言清除事件的坐标点。
登陆舱降落在旧都“言墟”边缘。这里曾是赤砂星最大的演讲广场,如今只剩下一圈环形石基,上面刻满了被磨平又重新凿出的字迹。风吹过时,沙粒摩擦石面,发出类似低语的声音。
她刚踏出舱门,便察觉异样。空气中飘浮着极细的金属丝,呈网状分布,随气流轻微摆动。这是“静默之网”??一种能吸收并中和声波的纳米结构,由政府维持运转,确保任何超过40分贝的声音都会被立即消解。
林小愿却笑了。
她举起竹笛,放在唇边。
没有吹奏旋律,只是轻轻呼出一口气。气流穿过笛腔,发出一声短促而干涩的“呜??”,像是一只幼鸟试飞前的第一声啼叫。
那一瞬间,整片沙地剧烈震颤。
金属丝网骤然扭曲,仿佛被无形之力撕扯。远处几座废弃塔楼轰然倒塌,扬起漫天红尘。而在沙暴中心,一道模糊的人影缓缓浮现??佝偻、迟疑,双手交叠于胸前,做出典型的“禁言礼”。
“外来者……”那人开口,声音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你知不知道……你说出了‘音’?”
林小愿放下笛子,静静望着他:“我知道。我也知道,你三十年没说话了。”
老人浑身一震,瞳孔剧烈收缩。
“你怎么……”
“因为你站在这里。”她轻声说,“而不是逃开。真正恐惧声音的人,不会留下听它响起。”
老人嘴唇颤抖,终于吐出一个词:“痛……”
接着是第二个:“我……痛……”
话音未落,他突然跪倒在地,双手抱头,仿佛有无数针刺入大脑。林小愿冲上前扶住他,感受到他体内传来一阵阵高频震动??那是植入脊椎的语言抑制器正在启动应急封锁程序。
她毫不犹豫,将竹笛贴在他后颈,指尖注入一丝魂力。这不是治疗,而是一种“共鸣劫持”??用笛声频率强行干扰神经信号传输路径。刹那间,老人喉咙里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嘶吼,不是痛苦,而是压抑了半生的呐喊。
那声音撞上静默之网,竟引发连锁崩解。一条条金属丝如枯藤般断裂、坠落,在空中化作灰烬。更多身影从废墟中探出头来,眼神惊恐又渴望。
林小愿扶着老人坐下,取出随身携带的素描本,在沙地上画了一幅简单的图:一个人张嘴,嘴里不是词语,而是一团火焰。
“这不是危险。”她指着画说,“这是活着的证据。你们不是失去了语言,是被教会了害怕它。可声音本身,从不伤害人??只有禁止发声的社会才会。”
夜幕降临,言墟燃起了第一堆篝火。三十一名赤砂人围坐一圈,每人手中握着一块陶片,上面刻着他们想说却从未敢出口的话。一位老妇人颤抖着念出自己写下的句子:“我想念我儿子的名字。”??那是她亲生骨肉,因在葬礼上哭泣过度被列为“情感失控行为者”,强制迁往隔离区,至今杳无音信。
林小愿听着,一言不发,只是将那段话录进笛身内的微型存储器。当最后一个声音落下,她再次举起竹笛,这一次,吹奏了一支极慢的曲子。没有乐谱,没有节奏规整,每一个音符都带着犹豫、停顿、甚至破音。但这正是她想要的??不完美的真实。
笛声传出去的瞬间,远在三光年外的启鸣号上,太极水晶猛然旋转,自动连接共生意志网络,将这段音频同步播送至所有已接入星域。零站在控制台前,闭目聆听,嘴角泛起一丝极淡的笑意。
“她说得对。”他对邹巧翰说,“我们不需要统一的语言,只需要统一的勇气。”
与此同时,赤砂星轨道外,一艘伪装成陨石的监察舰正悄然记录这一切。舰内,一名身穿黑袍的观测官冷冷注视着画面,手指悬停在“清除指令”按钮上方。
“目标已引发群体性语言复苏迹象,建议立即执行净化协议。”副官低声请示。
观测官沉默良久,最终缓缓收回手。
“再等等。”他说,“我想看看……她说完所有故事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吹笛。”
林小愿并不知晓这场暗中的凝视。她只知道,当第二天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言墟时,已有上百名赤砂人自发聚集,手中拿着各式自制乐器??陶埙、骨哨、铜铃、甚至只是空罐头盒。他们不会演奏,也不懂音阶,但他们愿意尝试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一个小女孩怯生生走到她面前,递上一支用红柳枝削成的短笛。
“我能……试试吗?”她问。
林小愿蹲下身,握住她的手:“当然可以。但记住,哪怕吹错了,也别停下。错的音,有时候比对的更接近真心。”
孩子深吸一口气,鼓起腮帮。第一声尖锐刺耳,像猫叫;第二声断断续续,几乎不成调。可当她第三次尝试时,一段极其简单的旋律流淌而出,稚嫩却明亮,宛如晨露滴落沙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