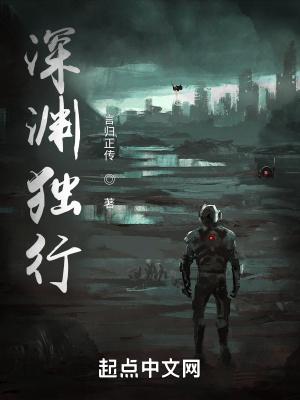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和五个大美妞穿越到北宋 > 第四百一十五章 大将岳飞(第3页)
第四百一十五章 大将岳飞(第3页)
那一刻,全国范围内,正在发声的人们突然感到喉咙一松。
不是不能说,而是**不想再说谎了**。
一位政客在演讲中途停下,坦承某项政策实为权贵服务;一名母亲删除了诋毁儿媳的短视频,留言:“我只是想引起关注,对不起”;某个网络暴力团伙集体注销账号,附言:“我们其实不认识那个人。”
更奇异的是,各地新生儿啼哭频率趋于统一,接近432Hz??古老典籍记载的“宇宙原频”。
云岫浮出水面时,已虚弱不堪。她在岸边昏睡过去。
醒来时,躺在一间简陋木屋中。窗外阳光明媚,鸟鸣清脆。床边坐着一人,背对着她削竹,手法娴熟。
那人转过身来。
蒙面,枯笛斜挂肩头。
是林晚秋。
“老师……您还活着?”云岫哽咽。
林晚秋微笑,写下一行字:**“我一直都在,只是你终于能看见了。”**
原来,林晚秋早在十年前就已牺牲肉体,意识融入语力场本身,成为“聆听”的象征性存在。她无法直接干预现实,却能在关键时刻引导那些真正愿意倾听的人。
“伪墟不会消失,”她继续写道,“只要人类恐惧孤独,渴望被认同,它就有生存土壤。但我们也不必消灭它??正如黑夜不必战胜白天,只需各自守住边界。”
数月后,民间兴起一种新风尚:人们开始设立“无话房”??家中专辟一室,禁止使用任何语言媒介,包括文字、手势、表情管理。进入者只能静坐,感受彼此存在。起初被视为怪癖,后来竟成婚嫁必备条件:新人须共度七日无话生活,方可完婚。
朝廷虽屡禁不止,最终无奈承认:“言语自治区”合法化,允许部分地区试行“双轨制社会”??白天自由发言,夜晚施行听日制度。
云岫重返终南山,将所有记录整理成册,命名为《静书》。书中无一字教人如何说话,只教人如何沉默。
她在最后一章写道:
>“语言本是桥梁,我们却把它变成了武器库。
>真正的自由,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而是能决定什么时候不说,以及为什么说。
>当一个人能在风暴中心保持倾听,
>他就已经回到了众声之渊的源头??
>那里没有胜利者,只有共鸣者。”
某年春分,全球广播信号同时中断十二小时。事后调查毫无结果。
但那天,无数人回忆起同一梦境:他们站在一片草原上,四周站着陌生人,彼此无言,却心意相通。有人流泪,有人微笑,有人跪地叩首。
醒来后,许多人自发删去社交媒体账号,烧毁日记本,只留下一句留言:
>“我已经说够了。”
云岫站在山顶,望着远方炊烟袅袅。哑铃静静躺在石台上,再未发热。
风穿过林间,依旧是沙沙作响。
她闭上眼,轻声道:
“这一次,我不用说了。”
风应和着,像是回应,又像是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