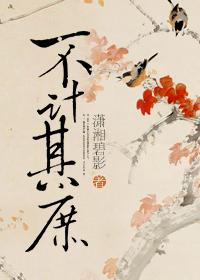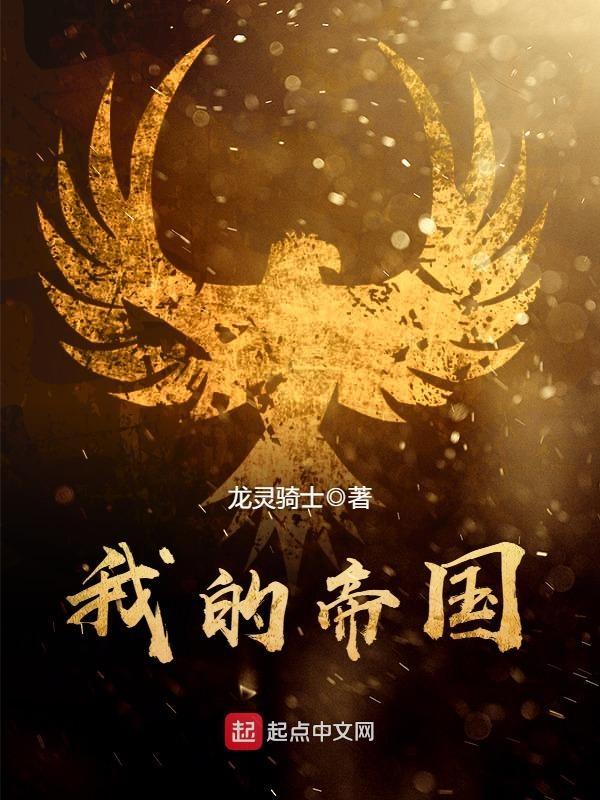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和五个大美妞穿越到北宋 > 第四百一十三章 小婿拜见岳父(第2页)
第四百一十三章 小婿拜见岳父(第2页)
就在此时,无字书忽然自动翻页,一张人脸缓缓浮现??竟是林晚秋。但她开口了。
“你们错了。”她说,声音温柔却冰冷,“真正的自由不是畅所欲言,而是有权保持沉默而不受惩罚。可你们把‘沉默’污名化了。现在,人人都害怕不做声,于是拼命发声,哪怕空话连篇。这正是‘伪墟’的养料。”
云岫怒极,冲上前欲毁书。可她的手刚触及封面,整座大厅骤然震动,青铜镜同时碎裂,碎片落地竟化作黑色蝌蚪状生物,迅速钻入考察队员耳鼻之中。数息之间,十余人眼神呆滞,开始齐声朗诵起官方编纂的《启言颂》:
“万民开口,天下光明;一语成谶,百世安宁……”
语调整齐得如同机械。
墨婉儿立即下令封闭洞口,全员撤离,并启动“镇魂鼓阵”环绕遗址建立声障。但她知道,这场战争已进入全新阶段。
敌人不再是强迫沉默的暴政,而是利用“言论自由”作为武器,制造虚假多元、情绪对立、信息泛滥的迷雾。人们越是急于表达,越容易落入陷阱??说出的越多,真实的自我反而越被稀释。
三个月后,全国爆发“喧语潮”。
街头巷尾,人人争辩不休。茶馆酒肆,三句话不合便拔剑相向。朝堂之上,谏官日奏三十疏,内容相互矛盾,只为博取关注。民间甚至兴起“骂战擂台”,胜者获赏千金,败者当众自扇耳光。更有商人推出“代诉服务”,雇人替客户写檄文、发宣言,不论立场,只论报酬。
而在这片喧嚣之中,真正重要的声音却被淹没。
边关急报称敌军压境,却被斥为“制造焦虑”;农夫上书请求减免赋税,被嘲讽“不够正能量”;孤儿院求援信贴满城门,无人问津,反倒是某官员抱怨茶水太凉的帖子登上热搜榜首。
云岫巡查途中目睹一幕:一名老妇抱着孙子尸体跪在衙门前哭诉,说孩子因误食含缄口墨的井水而失语致死。她手中举牌写着“还我公道”,可围观者纷纷拍照发帖,评论却是:“演得太假”“博同情”“建议去拍戏”。
她拔剑斩断牌匾,怒喝:“你们看不见吗?!”
人群哄笑:“看啊!又一个‘正义侠客’上线了!快录下来!”
那一夜,她独坐城墙,望着万家灯火,第一次感到彻骨孤独。
原来最深的压迫,不是不让你说,而是让你说了一万句,却没人听得见。
第四个月初七,墨婉儿寿终正寝。
临终前,她将毕生所记刻于七块黑晶,沉入太湖底。最后一口气息吐出时,嘴角竟带着笑意:“很好……他们终于开始怀疑自己说的话了……觉醒,从不信开始。”
她的葬礼没有哀乐,只有十二面铜鼓轮流敲击寂静节奏,象征“聆听即反抗”。
又过了两年,云岫接到边疆密报:西域出现一座移动沙城,城中居民皆戴面具,从不说话,仅以手势交流。但他们的眼神异常清明,行动高度协同,已在沙漠中建立十余个绿洲据点,收容各地逃离“喧语潮”的难民。
带队者是一位蒙面女子,据目击者描述,她从不发言,但每当众人陷入分歧,她只需轻轻吹响一枚短笛,所有人便会瞬间安静,继而达成共识。
云岫带上干粮与地图,孤身出发。
穿越戈壁第七日,她终于抵达沙城。守卫验明身份后,引她进入主帐。帐内陈设简朴,唯有一张矮几,几上放着半截枯笛。
那女子转过身。
云岫浑身剧震。
尽管面容苍老,尽管双目空洞,但她认得那挺直的脊梁,那沉静的气息,那即使不发声也令人不敢逼视的威严。
“老师……?”她哽咽跪下。
女子摇头,指了指耳朵,又指了指心,做了个“听”的手势。
然后,她取出那半截枯笛,贴于唇边。
没有声音。
但云岫忽然明白了。
她俯身拾起沙粒,在地上缓缓写下三字:
**“我在。”**
风起沙舞,字迹转瞬湮灭。
可那一刻,她觉得整个世界重新变得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