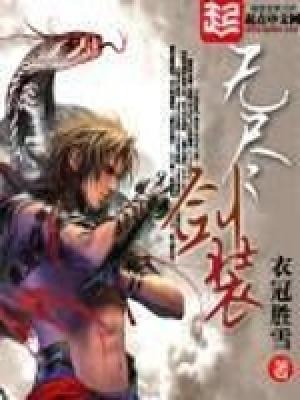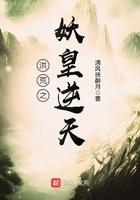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龙族:逼我重生,还要我屠龙 > 第476章 团伙开诚布公大会谈(第3页)
第476章 团伙开诚布公大会谈(第3页)
“你在读什么?”我忍不住问。
他抬起头,笑了笑:“我在听风翻页。”
我心头一震。
在他脚边,放着一块拇指大的静语晶,表面光滑,映着晚霞。
我坐下,没再说话。
我们就这样并肩坐着,看太阳落下,星辰升起,湖面由金变银,再归于幽暗。
不知过了多久,老人轻声说:“你知道吗?我儿子十年前死于战场。临终前录音里一直在喊,喊战友的名字,喊妈妈,喊上帝……可我一直恨那段录音,因为它让我听见了他的恐惧。”
我转头看他。
“但现在我不听了。”他说,“我把录音删了。取而代之的是每天来这里坐一会儿。我发现,当他真正想跟我说话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声音。”
我点点头。
“他也在这里。”我说。
老人侧目:“谁?”
“所有不肯再说的人。”
夜深了,湖边亮起一圈低矮的地灯,柔和如月光。远处钟楼敲响九下,但没有鸣响,只有指针轻轻转动的投影划过天空。
我起身告别。
老人挥挥手:“下次再来,带一本空白的书吧。”
我微笑:“好。”
步行穿过市中心,街道比记忆中安静得多。广告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动态水墨画般的自然影像;行人戴着非降噪耳机,但用途不是隔绝噪音,而是放大心跳与呼吸的节奏;咖啡馆里,情侣相对而坐,不说话,只是轮流在桌上写下一句话,然后撕掉,继续写。
走到旧总部大楼前,我停下脚步。
逆铃塔已改造成一座螺旋形玻璃建筑,外墙刻满各国文字中的“静”字。门前广场中央立着那块尚未完工的纪念碑,工匠正在雕刻最后一笔。
一名年轻女子走来,穿着实验服,胸前挂着工牌:**静语学院?首批教师培训营**。
“林校长。”她行礼,“课程大纲已初步拟定。第一课叫《如何忍受不说出答案》。”
我笑出声:“很好。第二课呢?”
“《当你想打断时,请先数到六十六。》”
“六十六?”我挑眉。
“因为那是地核脉冲的周期,也是静默之子诞生的节奏。”她认真道,“我们打算把它定为‘标准静息单位’。一‘息’等于六十六秒纯粹的无干扰状态。”
我点头:“可以。再加一门实践课:《与陌生人共处一室而不交谈》。”
“已经在排课表了。”
她递给我一份文件:“另外,全球申请入学的孩子已达十万。我们按‘梦境报告’筛选首批学员??凡是梦见过桥、深渊、光门、或听见母亲呼吸声的,优先录取。”
我翻开名单,手指停在一个名字上。
**陈小禾**。
男孩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