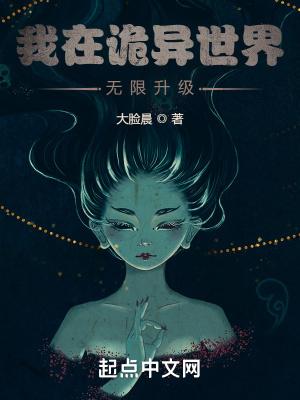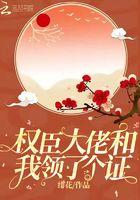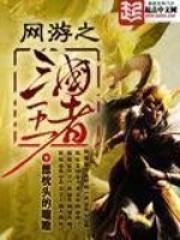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重启人生 > 0512还是老罗靠得住(第2页)
0512还是老罗靠得住(第2页)
>“爸,我梦见你回来那次,穿着西装,提着行李箱。你说‘儿子,爸爸只是出差久了’。我扑上去抱你,可你突然消失了。我跪在地上哭,醒来枕头全是湿的。
>医生说我这是‘创伤性哀悼障碍’,听起来像个罪名。可我只是……想再看你一眼。
>舅舅说我该懂事,我妈说我别拖累她新家庭。没人问我疼不疼。
>今天听了那些话,我才明白??原来不是我疯了,是我太想你了。
>爸,我不是故意不哭的。我只是怕,一旦开始哭,就再也停不下来。”
录音结束,他趴在桌上,肩膀剧烈起伏,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许风吟轻轻盖上录音机,递过一杯温水。“你知道吗?”他说,“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延迟哀悼’??有些人不会立刻悲伤,因为他们必须先学会活下去。你不是冷漠,你是用沉默扛住了整个世界的重量。”
周远抬起头,眼里布满血丝:“可我现在撑不住了。”
“那就允许自己倒一次。”许风吟说,“在这里,在这个房间里,你可以倒。”
男孩终于崩溃大哭,像一座压抑多年的火山猛然喷发。许风吟没有劝他停下,只是静静坐着,任泪水浸透地板。
第二天清晨,许风吟在《回声档案》第六十九页写下:
>**周远,14岁。
>他在父亲死后学会了不哭,
>在母亲离去后学会了不说,
>在老师否定中学会了自我惩罚。
>直到那一晚,他终于对着一台旧录音机,喊出了积压三年的思念。
>他的伤口不是自残的疤痕,
>而是从未被允许哀悼的失去。
>如今,他的眼泪不再是软弱的证明,
>而是对父亲最深的告白。
>而他的声音,已被我们小心收藏,
>等待某一天,由他自己亲耳听见。**
中午,赵医生带来消息:校方决定设立常驻心理咨询室,并申请专项资金培训教师心理干预能力。“更重要的是,”她说,“周远的母亲昨天打了电话回来。她说她看了我们的匿名音频汇编,听到那段‘你自己,对不起’时,哭了整整两个小时。她想见儿子,哪怕只是视频。”
许风吟点头:“有时候,父母也需要被唤醒。他们不是不爱,而是被困在了自己的痛苦里。”
午后,他们组织学生做“时间胶囊”活动。每人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封进铁盒,埋在校门口的老槐树下。周远写完后犹豫许久,最终多塞了一张纸条进去。
许风吟瞥见上面写着:
>“给十年后的我:
>如果你还记得爸爸,请带一束白菊去他坟前。
>如果你过得不好,请记住??
>昭通的那个夜晚,你哭过,也被人听见过。”
离开云岭中学那天,天空放晴。学生们站在校门口挥手,不少人眼里含泪。周远没来送行,但班主任送来一个信封:
>“他说,谢谢你们让他知道??
>哭,也可以是一种力量。”
车轮重新转动,驶向下一站。山路崎岖,阳光透过云层洒落,斑驳陆离。张老师翻看地图:“下一站,四川凉山州,美姑县。一所彝族村小,孩子们大多只会说母语,汉语沟通困难。但他们有一个传统??每年火把节,会把心愿刻在松枝上,点燃后抛向星空,说是‘让神听见’。”
赵医生轻叹:“语言不通,不代表没有声音。有些痛苦,比话语更深。”
许风吟望着窗外飞逝的群山,忽然说:“我们带些录音笔去吧。让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我们负责翻译、记录、传递。哪怕听不懂词句,也能听见心跳。”
三天后,他们抵达村子。火把节前夕,全村老少聚集在广场。孩子们围着篝火跳舞,脸上涂着彩绘,眼中闪烁着久违的光。许风吟拿出录音笔,蹲在一个小女孩面前,用手比划:“你想对你阿嫫(妈妈)说什么?”
女孩怯生生接过话筒,低头想了好久,终于开口,用彝语喃喃:
>“阿嫫,你走的时候说要去打工,很快回来。可是五年了,我连你的照片都快记不清了。
>我每天帮你喂鸡,扫地,煮饭。弟弟生病了,是我背他走十里路去看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