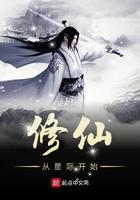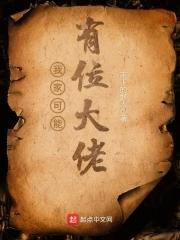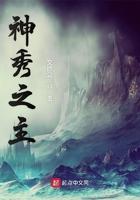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重启人生 > 0503陈老祖的互联网传奇(第4页)
0503陈老祖的互联网传奇(第4页)
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许多年前,他自己蜷缩在房间角落,渴望有人能听见那句未曾出口的“救救我”。
如今,他成了那个听见的人。
秋天来临时,“百校千灯”覆盖全国三十二个省份,累计建成1378个“声音角落”。教育部将其纳入心理健康教育示范项目;央视制作专题纪录片《听见》,播出当晚收视破纪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函致谢,称其为“草根级心理援助的东方样本”。
但在许风吟心中,最重要的时刻发生在某个普通周三。
那天,阿木寄来一封信,信封里夹着一张照片:他站在县中学的讲台上,身后黑板写着“新生分享会”五个大字。照片背面是他稚嫩却坚定的字迹:
>“今天我讲了自己的故事。
>下课后,有个女生哭了,她说她妈妈也走了。
>我把那只蓝船送给了她。
>原来,被照亮的人,也能成为光。”
许风吟把照片贴在《回声档案》扉页。
他知道,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个孩子终于敢抬头看天,一只纸船漂过千山万水,一句“我在”穿越漫长孤寂。
冬至那天,他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附件是一段音频。
播放后,竟是三年前那位抑郁症少年的声音。如今他已经十八岁,考上了师范大学。
>“各位曾经听过我声音的朋友:
>明天我就要去实习学校了,教语文。
>我准备的第一课,就是阿木的作文。
>我想告诉我的学生:
>写作不是为了得分,是为了不让心里的话烂掉。
>谢谢你们当年没有关掉我的录音。”
许风吟关上电脑,走到阳台上。城市灯火依旧璀璨,广告屏再次亮起,这次的画面不同了:不再是单向倾诉,而是双向奔赴??孩子把纸船放进溪流,另一端,成年人弯腰拾起,读完后郑重回信。
旁白换了声音,是一个小女孩:
>“你说出的话,也许要走很远很远。
>但它终会找到回家的路。
>因为这个世界上,
>总有人,正在等你开口。”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寒冬的空气刺入肺腑,却让他感到清醒而有力。
明天,他又将启程。
下一站在甘肃,一个黄土高原深处的小村。
据说那里有个男孩,连续三年在作文里写同一句话:
>“如果风能传话,
>我想问问爸爸,
>为什么每年清明,坟前的花都是别人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