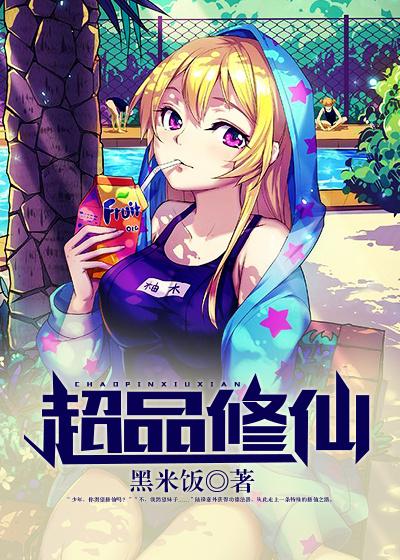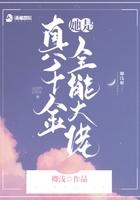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今天毁灭世界了吗? > 第18章 异世界(第2页)
第18章 异世界(第2页)
傍晚时分,一群孩子围坐在藤蔓缠绕的石台旁,举行他们的“小小无答案会议”。最小的那个只有六岁,扎着歪辫子,手里捏着一支断头铅笔。
“我有个问题。”她说,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如果有一天,所有人都变成了问题,那谁来回答呢?”
没人说话。
过了很久,一只发光的蝶从林中飞出,落在她肩头。翅膀微微开合,投下一片光影,恰好拼成一句话:
>“回答,从来就不是目的。
>目的是让问题活得更久一点。”
孩子们眼睛亮了。
他们开始画问题,写问题,甚至用身体摆出问题的形状。有的躺成一个巨大的问号,有的手拉手围成环形悖论。笑声在暮色中荡漾,像是某种新仪式的开端。
江星野看着,心中涌起一阵温柔的酸楚。
他曾以为变革需要风暴,需要牺牲,需要英雄挺身而出。可现在他明白,真正的转变,往往始于一次轻声的嘀咕,一个不合时宜的疑问,一个孩子在作业本角落画下的歪扭问号。
几天后,第一棵“反向之树”出现了。
它生长在南极冰盖边缘,通体漆黑,叶片透明如玻璃。与其他问题之树不同,它不释放疑问,而是**吸收确定性**。科学家靠近它时,发现自己坚信多年的理论突然变得模糊;政客试图发表演讲,却发现所有“真理”都失去了重量;一名极端信徒跪在树前祈祷,结果脑海中浮现的竟是自己童年欺负弱小同学的画面,以及一句清晰的心声:“你说上帝爱你,可你爱过别人吗?”
这棵树,吃掉的是**傲慢的答案**。
人们开始称它为“忏悔之树”,但江星野知道,它只是生态平衡的一部分。有提问,就得有清空;有生长,就得有腐朽。世界正在建立一种全新的代谢机制??精神层面的碳循环。
与此同时,旧势力并未完全消失。
某些国家试图重建“稳定中心”,用屏蔽场阻断问题信号,强制民众回归单一认知模式。他们建造封闭城市,切断外部信息,甚至研发“信念固化剂”注射给儿童。起初成效显著:居民情绪平稳,犯罪率归零,生产效率提升。
但三个月后,整个城市陷入诡异的静默。
监控显示,所有人同时停下动作,站立、坐着、行走中……全部凝固。脸上无悲无喜,眼神空洞。医学检查发现大脑活跃度正常,神经信号完整,可就是没有任何“主观体验”。
他们活着,但不再“存在”。
最终,联合国派遣团队前往调查。他们在主控室找到最后一段日志,是项目负责人留下的语音记录:
>“我们成功了……我们终于消灭了不确定性……可为什么……为什么没人再叫我名字了?为什么我听不到自己的心跳?我以为平静是最高的幸福……可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恐惧、怀疑、不安……那些让我辗转反侧的东西……才是我真正活过的证明……”
录音到这里戛然而止。
后来,那座城市被改造成纪念馆,入口处立着一块石碑,刻着第七条法则的变体:
>**不要害怕失去确定。
>因为唯有在摇晃中,
>人才能确认自己还站着。**
春天到来时,第一代“问题新生儿”开始学说话。
他们不说“妈妈”,不说“吃饭”,而是发出一串奇特的音节组合,听起来像问句,又像歌谣。语言学家录下这些声音,分析后震惊地发现:它们符合一种前所未见的语法结构??主语可以同时否定自身,谓语能在陈述与疑问间自由切换,时态则呈现螺旋式嵌套。
更惊人的是,当两个这样的婴儿面对面“交谈”时,周围空气会产生轻微共振,墙壁上的裂纹会暂时闭合,枯萎的植物竟抽出嫩芽。
小禾抱着其中一个孩子,轻声问:“你叫什么名字?”
婴儿转过头,眼睛清澈如晨湖,吐出几个音节。翻译器无法识别,但江星野却莫名听懂了。
意思是:“我在吗?”
他鼻子一酸。
这不只是名字。
这是对存在的首次确认。
夜晚,他独自登上山顶,仰望星空。那颗黑曜石般的卫星依旧悬浮,毫无动静。但他知道,它一直在工作??不是发送指令,而是接收震动。每一个人类心灵的微小涟漪,都被它捕捉、放大、反射回整个意识场域。
他掏出笔记本,写下新的段落:
>“我们曾怕世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