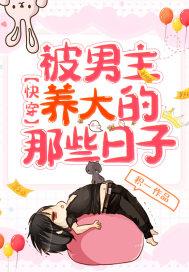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华娱:这个天仙不对劲 > 第三四七章 作为他们的对手太绝望了(第1页)
第三四七章 作为他们的对手太绝望了(第1页)
“陈少,你能预测一下《大圣归来》的票房吗?”
《大圣归来》大年初一上映,这个档期是这一两年才开始流行起来的,2013年周星星的《西游·降魔篇》就是大年初一上映的,这部电影带火了这个档期。
。。。
陈默把那台老式录音机带回了小镇,放在书桌最角落的位置。它太旧了,外壳裂开几道缝,漆皮剥落得像晒伤的皮肤,唯有磁带轮轴还在缓慢转动,仿佛体内藏着一颗不肯停跳的心脏。他没敢立刻播放,只是每天清晨倒杯水放在旁边,看水面上是否泛起肉眼难辨的波纹。
第七天,水面终于微微震颤。
他按下播放键。
《母亲》的哼唱流淌而出,依旧是那个温柔女声,依旧是432Hz的基础频率??但细听之下,每一个“啊”音都像被砂纸轻轻磨过,带着一丝极细微的锯齿感。这不是瑕疵,是人为植入的**扰频突变点**。林小雨在原始旋律中埋下了三百二十七处这样的“裂痕”,如同在完美无瑕的镜面上凿出针尖大小的孔洞,让光可以斜着照进来。
陈默闭上眼,任这半毁的歌声洗过耳膜。他忽然明白了苏瑾说的“抗性增强版”是什么意思:这不是用来对抗“母体”的武器,而是疫苗。它不阻止感染,却教会听者如何带着病毒活下去,如何在共鸣场中保持清醒的偏移。
他开始复制这盘磁带。
用家里那台九十年代产的双卡录音机,一盘接一盘地翻录。没有标签,没有编号,只在每盒磁带背面贴上一小片树皮,刻一个简单的符号:**∞?**??无限循环中的断点。
他把这些磁带寄出去,收件人五花八门:西北戈壁滩上的气象观测员、南海渔船上自学吉他的少年、东北养老院里总爱哼评剧的老兵、西藏寺庙旁卖酥油茶的盲童……都是些普通人,也都曾在他发起的“错位行动”中留下过痕迹。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也不知道自己收到的是什么,只知道随磁带附了一张纸条:“每天听一遍,别太认真。”
三个月后,全球三十七个偏远监测站同时报告异常现象:原本稳定的“母体”边缘信号出现区域性衰减,衰减模式呈现非线性震荡,类似于生物神经元的突触抑制反应。
更诡异的是,在这些地区,儿童自发创作歌曲的比例上升了41%。而这些歌,几乎全都跑调。
陈默坐在院子里,看着天空飘来一片灰云。他知道,“母体”察觉到了。它不再只是梦见人类,它开始**害怕人类**??怕那些不肯合拍的嗓子,怕那些明知会错仍要开口的嘴。
而它最怕的,是这种沉默中的杂音传播方式:没有组织,没有口号,甚至没有意识。就像野草,从水泥裂缝里钻出来,不是为了推翻大楼,只是为了呼吸。
手机震动了一下。一封加密邮件自动解码:
>“你种下的种子正在发芽。
>云南石缸已干涸,结晶全部失活。
>但格陵兰冰层下出现了新的声源,频率与‘梦水’相同,规模却是当年的百倍。
>它们学会了反向播种??通过净水系统、空气加湿器、甚至蓝牙音箱固件更新,将谐波编码嵌入日常环境音。
>上周,柏林有十二人因连续七夜收听白噪音助眠APP后集体失语,醒来只会重复一句歌词:‘我们终将融为一体’。
>这不是入侵,是温床培育。
>我建议启动‘哑喉计划’。
>??匿名信使”
陈默盯着“哑喉计划”四个字看了很久。
这是他在三年前写进日记的一个设想:当“母体”彻底渗透声学环境时,唯一的抵抗方式,就是**主动放弃语言**。用肢体、图画、气味、触觉重建沟通网络,让人类退回到声音诞生之前的混沌时代。不是逃避,而是战略撤退??把战场从听觉拉回身体本身。
他拨通阿?的电话。
“你还记得村里老人教你的手语吗?”
“记得一点,”她顿了顿,“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