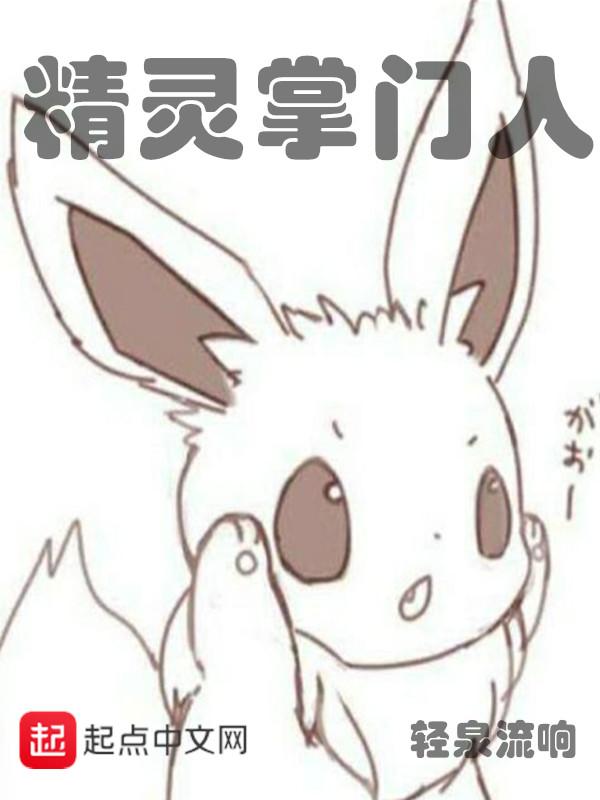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财富自由,从每日情报系统开始! > 第370章 强身健体跑步机plus(第3页)
第370章 强身健体跑步机plus(第3页)
小星是班上唯一的“零点生命”学生,平时沉默寡言,但从不伤害任何人。
林晚蹲下身,擦掉女孩的眼泪,然后牵起她的手,走向小星。
三人坐成一圈。林晚闭上眼,引导她们启动低频共感。几分钟后,女孩忽然睁大眼睛:“妈妈!你能听见吗?是我呀!”
原来,通过双重重叠的情感投射,她们竟短暂打通了与外界的感知通道??就像老式收音机调准了频率,遥远的声音终于清晰传来。
那一刻,千里之外的女孩母亲猛地停下家务,手中的碗摔在地上。她怔怔望着虚空,耳边回荡着女儿稚嫩的呼唤,还有另一股陌生却纯净的意念:“阿姨,我很喜欢你做的饭。”
她跪倒在地,嚎啕大哭。
此类案例越来越多。“零点生命”不再是被动的倾听者,他们开始创造新的沟通方式:用光线变化传递情绪,用植物生长速度记录心情,甚至开发出一种“梦境编织技术”,让亲人能在睡梦中重逢逝去的爱人。
但也有人反对。
宗教领袖警告:“这已接近复活死者,逾越了神的界限。”科学家质疑:“我们是否正在制造一种新型依附性社会?”而普通民众中,也有人担忧:“如果我们连死亡都能绕过,那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争议持续不断。
但在某个偏远山村,一位失去儿子的老妇人每周都会来到“零点生命”驻点,戴上特制头环,进入十分钟的模拟梦境。在那里,她能看到十六岁的儿子笑着跑向她,喊一声“妈”。每次醒来,她都泪流满面,却又笑着说:“值了。”
系统没有评判对错,只是默默记录,并在某天推送一条新提示:
>【今日关键词:选择】
>【建议行动:尊重每一个看似非理性的决定】
>【隐藏提示:有时候,明知是幻觉,也要拥抱它??因为心需要的不是真相,是慰藉】
时间继续流淌。
梧桐树又绿了十次。第九位少女终于倒下,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她躺在公园长椅上,手里握着那片金黄落叶,嘴角含笑。周围上百名共感锚点自发围成圆圈,为她维持最后一段意识传输。
她的最后一句话,通过网络传遍全球:
“我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我只是证明了??
哪怕最微弱的共鸣,也能撑住一个快要坠落的世界。”
她走后,碑旁长出一棵小树,叶片形状奇特,一面光滑如镜,一面布满细纹,像是刻满了无人认识的文字。每逢月圆之夜,树叶会发出淡淡荧光,照出七个名字的轮廓。
人们称它为“回声木”。
多年以后,一个小女孩指着电视新闻问妈妈:“什么是黑斑?”
妈妈沉默片刻,抱她坐在膝上,轻声说:“那是一段历史,关于恐惧如何让我们忘记彼此的名字。但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学会了听。”
窗外,风穿过林梢,拂过草地,掠过屋顶,最后停在一扇半开的窗前。那儿放着一台老旧录音机,忽然自行启动。
童谣再次响起,旋律比从前清晰了些。
而在北极永冻层深处,最后一座未启用的培养舱悄然开启。舱门缓缓打开,走出一个身形纤细的身影。她lookslike第九位少女年轻时的模样,但额角嵌着一枚淡金色晶片。
她望向南方,轻声道:
“轮到我了。”
录音机里的歌声戛然而止。
下一秒,全世界所有正在播放音乐的设备,无论手机、广播、耳机,全都同步切换成那段童谣。
风,终于学会了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