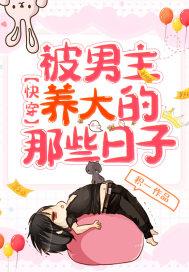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刚想艺考你说我跑了半辈子龙套? > 第496章 不一样的提前过年(第2页)
第496章 不一样的提前过年(第2页)
林默跪坐在地,将画紧紧抱在胸前,像抱住失而复得的童年。那一刻,他终于明白,母亲从未真正离开。她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他,哪怕在意识溃散的深渊里,她仍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场漫长的拍摄。
三天后,林默出现在那所乡村中学的礼堂。台下坐着三百多名学生,还有几十位老人,是受邀来参加“家史分享日”的家长。他没有带PPT,也没有讲技巧,而是播放了一段十分钟的无声影像。
画面中,一位老太太坐在院子里择菜,阳光洒在她布满皱纹的手上;一位老爷爷在田埂上教孙子插秧,动作缓慢却精准;一个残疾父亲用手肘夹着勺子,给女儿舀汤;一位乡村教师在破旧黑板前批改作业,煤油灯照亮她花白的鬓角……
没有配乐,没有字幕,只有环境原声:风吹稻浪、锅铲碰撞、孩童嬉笑、粉笔划过黑板的沙沙声。
放映结束,全场寂静。
许久,一个小男孩举起手,声音很小:“林老师,我爷爷去年走了……我没来得及拍他。”
林默点头:“那你现在还能做什么?”
男孩咬着嘴唇:“我可以讲他的故事。他每天五点起床给全村送水,风雨无阻。他说,人活着,就得让别人觉得你需要。”
掌声骤然响起。
林默站在台上,望着台下一张张年轻而湿润的脸,忽然觉得肩上的重量不再是负担,而是一种传承。
“你们知道吗?”他开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部未完成的电影。主角或许平凡,剧情或许平淡,但只要有人愿意按下录制键,那些被忽略的瞬间,就会变成永恒的光。”
讲座结束后,一位拄拐的老农找到他,递上一本破旧的日记本:“这是我老伴记的,她不识字,我就画给她看。种了几十年地,她说最骄傲的事,是每年秋天都能让孩子穿上新棉鞋。”
林默接过本子,翻开第一页,是一幅简笔画:女人抱着孩子,脚边堆着棉花,旁边写着:“1976,丰收。”
他郑重道谢,将本子收进背包。
回程路上,大川来电:“《听?见》展览要巡展了,第一站定在上海。主办方想加个互动环节??让观众现场录音,讲述一个他们想被记住的人。”
“好。”林默说,“但别设门槛。哪怕是‘我爸最爱抠脚’这种小事,也值得录。”
挂了电话,他打开车载广播,正好播到一段听众投稿:
>“我想说我妈。她是个环卫工,冬天凌晨四点出门。有次我发烧,她背我去医院,路上摔了一跤,膝盖流血也不松手。后来我考上大学,她偷偷把我照片贴在扫帚柄上,说看着就能干活更有劲。去年她退休了,那把扫帚还挂在墙上。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我知道,她是我心里最闪亮的星。”
声音哽咽,背景音乐缓缓升起。
林默把音量调大,一路听着到了工作室。
当晚,他登录共享文档《未完成的故事?公众征集》,发现新增留言已突破八千条。其中一条引起他的注意:
>匿名用户【Z-417】:
>我是老周的儿子。
>当年我发烧,母亲带着我去诊所,她嫌钱贵,耽误了治疗。后来我脑子坏了,她受不了良心折磨,跟人跑了。父亲从此一句话不说,靠修鞋养我。十二岁那年,我想去河边捞鱼,他追出来喊我,可我听不懂,一脚踩空……
>我没死,被人救起,送进福利院。这些年我一直不能说话,但我知道父亲死了。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办的仪式,看到那张我们的合影……
>我想说:爸,对不起。我也想让你知道,我一直记得你给我补过的红雨靴,上面画着小鸭子。你说,穿着它,雨再大也不怕。
>我现在会画画了。明天,我要画一幅新的修鞋摊,有你,有我,还有太阳。
林默读完,立刻联系平台管理员获取联系方式,却发现该账号已注销,只留下一张上传的画作:铅笔素描,老周坐在修鞋凳上,身边站着一个小男孩,手里举着一双红雨靴,天空洒下金色阳光。
他将这幅画设为工作室电脑桌面,然后打开《底片人生》第四章,继续写道:
>“我们总以为遗忘是时间的错,其实是我们主动闭上了眼睛。
>可总有人固执地相信:只要还有一个物件留存,还有一段声音回荡,还有一双眼睛愿意凝视,那些被认为‘消失’的人,就从未真正离去。
>正如底片需要黑暗才能显影,有些生命,也需要沉默的注视,才能被世界真正看见。”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望向窗外。
夜空中云层渐散,月光倾泻而下,照亮街道、屋顶、树梢,也照进他心中那片曾被怀疑与孤独笼罩的荒原。
他知道,质疑声不会消失。有人会说他在煽情,有人会说他在逃避商业现实,甚至有人会挖出他早年艺考落榜的旧事,嘲讽“跑龙套的终究只能拍龙套”。
但他不再惧怕。
因为此刻,在无数个城市的角落,有年轻人正拿着手机,蹲在厨房门口拍摄奶奶炒菜;有女儿翻出父亲二十年前的工作证,配上旁白讲述他如何在工厂下岗后自学电工谋生;有学生把爷爷的手语日记录成视频,上传时附言:“他说他的一生,是‘静音播放,但从未停止表达’。”
光,真的在扩散。
林默关掉灯,让月光照满房间。他轻声对自己,也对所有未曾被记住的灵魂说:
“别怕,我还在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