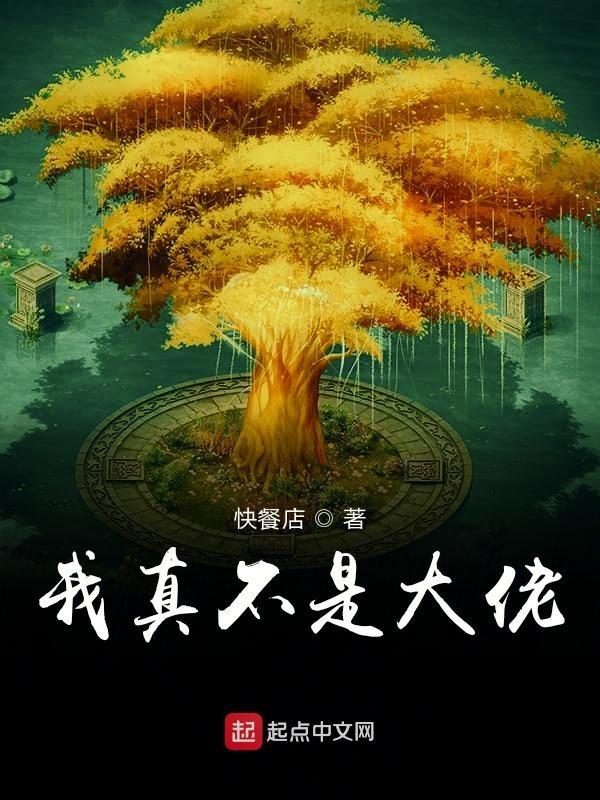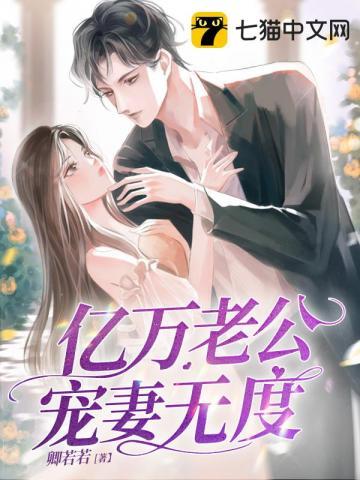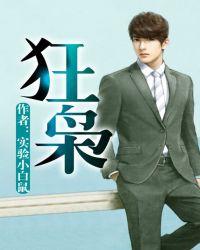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让你下山娶妻,不是让你震惊世界! > 第1644章 许久不见的雍古(第5页)
第1644章 许久不见的雍古(第5页)
医院里,植物状态患者苏醒率提升百分之十七;
校园霸凌事件减少,学生互助行为显著增加;
灾难救援现场,陌生人之间的协作效率前所未有地提高。
人们开始习惯在睡前播放那段童谣,称它为“安眠频率”。
有人把它编成舞曲,有人谱成交响乐,还有艺术家用它创作全息投影展览,主题叫《我们从未真正告别》。
而安禾,依旧每天清晨走进花园,记录花朵的动静。
某日黄昏,她发现茉莉藤蔓上开出一朵从未见过的花??花瓣半透明,脉络呈淡金色,每当风吹过,便会散发出极微弱的声波振动,频率恰好与那段童谣吻合。
她轻轻抚摸花瓣,低声问:“是你吗?”
花不动,却有一阵风穿过庭院,吹动屋檐下的风铃,叮咚作响,竟连缀成一句清晰话语:
>**“我在这里,也在everywhere。”**
她笑了。
当晚,她召集所有学生,在花园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仪式。
没有演讲,没有灯光,只有十二个孩子围坐一圈,每人手中握着一片听语草叶,闭目静听。
风起时,七朵花同时摇曳,叶片摩擦发出沙沙声,渐渐汇成一首无人指挥的合唱。
一个八岁男孩忽然睁开眼,轻声说:“我看见他了。”
众人望向他。
“他就站在我奶奶身边。奶奶三年前去世了,可刚才,我清楚看到她牵着他的手,对我笑。”
安禾没有质疑。
她只是轻轻握住男孩的手,点点头。
多年后,那位年轻记者再次来到云坪村,带着一本书稿来找她。
书名是《守门人:一个关于爱与牺牲的现代传说》。
他问:“我可以写下去吗?”
安禾望着花园,夕阳正洒在那朵金色茉莉上,光芒流转,宛如星辰坠落人间。
“写吧。”她说,“但别把他写成神。他只是个选择了倾听的人。”
记者点头,转身离去。
风起,花动,铃兰轻颤,仿佛在低语。
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某个母亲正哄孩子入睡,哼着一段模糊却温暖的旋律。
那调子不成章法,却隐隐合着某种古老的节奏。
像是回应,又像是传承。
而在更深的地方,在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缝隙里,有一个声音始终未曾消散:
>*“星星落,月亮摇,
>哥哥背着弟弟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