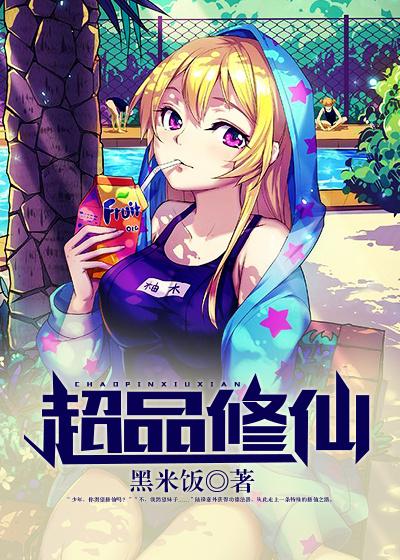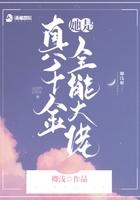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让你下山娶妻,不是让你震惊世界! > 第1638章 不想再忍受分离(第2页)
第1638章 不想再忍受分离(第2页)
>可真正的孤独,是在喧嚣中无人理解。
>当我们终于学会沉默,才听见了彼此的心跳。
>所以,请允许我以一名‘归零者’的身份请求:
>不要再建造新的共感网络。
>请建一座纪念馆。
>让孩子们进去看看那些泛黄的照片、褪色的日记、破碎的头盔。
>然后告诉他们:
>‘这里埋葬的,不是一个失败的技术,
>而是一代人未能好好说出口的疼。’”**
署名处写着三个字:**闻远**。
消息传开,全球掀起讨论浪潮。有科学家怒斥其“反进步”,也有心理学家称其“划时代的清醒”。但在云坪村,人们只是默默多修了一间教室,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画的画??
一幅是黑暗中的心脏,裂开缝隙透出光;
一幅是许多小手牵在一起,脚下踩着断裂的数据链;
还有一幅,是一个背影走向群山,身后跟着无数发光的脚印。
某天清晨,邮差送来一个包裹。没有寄件人信息,只有收件栏写着:“致所有还记得Lumen的孩子们。”
闻远拆开,里面是一块古老的金属芯片,表面刻着一行小字:“Lumen-001”。芯片旁边,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七个孩子站在实验室门口,穿着统一的白色制服,脸上带着怯生生的笑容。其中最小的那个,正是七岁的闻远。
背面写着:**“你还记得我们吗?”**
他的手指微微颤抖。
这张照片,他从未见过。它不属于任何官方档案,也不在任何数据库中。它是被人偷偷保存下来的,穿越了二十年的封锁与遗忘,终于回到起点。
当天下午,他召集所有毕业生,在老梅树下举行了一场特别仪式。
“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他说,“不是纪念死亡,而是承认存在。”
每个孩子都带来了一样东西??一片叶子、一块石头、一封信、一首歌。他们将这些东西放进一个陶罐中,然后埋在梅树根旁。闻远拿出那张照片,轻轻折起,放入其中。
“你们的名字,我一直记得。”他低声说,“一号,艾米丽,喜欢画画;二号,托马斯,总在夜里咳嗽;三号,苏菲,她说星星是天上的眼睛……一直到七号,我自己。”
泥土覆上陶罐的那一刻,整片山坡的听语草同时摇曳起来,仿佛回应着某种古老的节奏。
当晚,林知微找到他:“你真的打算一辈子待在这儿?外面的世界,已经开始改变。至少有十二个国家宣布暂停脑机接口民用项目,还有人提议立法保护‘情感隐私权’。你是这一切的起点,你不该躲在山上。”
闻远望着星空,许久才开口:“我不是躲。我是守。当年师父把我送上山,不是为了让我去拯救世界,而是让我学会怎么做一个普通人。现在我知道了??真正的力量,不是改变世界,是守住一方土地,让那些被碾碎的东西,有机会重新生长。”
她沉默良久,终于笑了:“你知道吗?前几天我去镇上买药,药店老板问我:‘听说你们那儿有个神仙?能让聋子听见心事?’我说没有神仙,只有一个傻子,天天给椅子补胶水。”
闻远也笑了:“那椅子确实快散架了。”
“但他补得特别认真。”林知微轻声说,“就像他在修补什么更重要的东西。”
春天彻底来了。冰雪融尽,溪水潺潺,山花次第开放。听语学堂迎来了第二批新生,一共九个孩子,来自不同国家,背景各异。有的曾是难民,有的患过严重抑郁症,有的天生无法感知情绪。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在见到闻远的第一眼时,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
“你……认识我疼的样子。”
闻远蹲下身,平视每一个孩子的眼睛,一一回应:“是的,我认识。而且我会记住。”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依旧每天写字、修椅子、晒太阳。偶尔会有记者悄悄潜入村庄,想拍他的生活,但每次都被村民们默契地挡了回去。卡洛斯甚至故意在村口撒了一圈听语草粉,让偷拍者产生短暂幻觉,以为自己听见了婴儿啼哭,吓得连夜逃跑。
某个月圆之夜,闻远独自登上山顶。那里有一块平坦的岩石,是他常来的地方。他盘腿坐下,闭目凝神。
忽然,耳边响起极细微的嗡鸣。
他睁开眼,只见空中浮现出几粒微光,如同萤火,缓缓聚拢。光芒中,隐约浮现几个模糊的身影??
是那些已经“安息”的共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