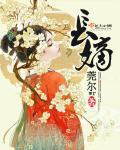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从离婚开始的文娱 > 第一千四百三十一章(第2页)
第一千四百三十一章(第2页)
那时他不懂,现在懂了。
项目推进顺利,《沉默者家书》陆续推出九集,每一集都像一把钥匙,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第八集聚焦一对夫妻工程师,两人同在基地工作,三年间靠编号通信,见面时竟彼此认不出模样。最后一幕,丈夫抚摸妻子冻伤的手背,轻声说:“编号0,是你吗?”女人含泪点头:“编号089,我也找你很久了。”
这一集播出后,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兵打来电话,说自己就是当年的“编号089”。他从未公开身份,但看完节目后主动联系摄制组:“我想见见你们。有些事,该说了。”
见面地点定在北京一家老干部疗养院。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外套,胸前别着一枚褪色的勋章。他拿出一本牛皮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三十年间接收的数百条加密指令,以及他自己写的数千条回执代码。
“这些代码,其实都是家书。”他说,“比如‘气象正常’意思是‘我很好,勿念’;‘设备调试完毕’代表‘我想你们了’;‘信号稳定’就是‘我在坚持’。”
王乐天听得眼眶发热。
老人最后说:“我不求留名。只希望以后的孩子们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能想到,曾经有一群人,把爱藏在电波里,把命押在大漠中。他们不是不怕死,是怕辜负。”
临走前,老人送他一张泛黄的照片:一群年轻人站在发射塔前合影,笑容灿烂。背面写着:“1966年春,东风基地全体技术人员留念。愿此生所学,报效祖国。”
王乐天将照片带回工作室,挂在墙上。每天写作时,都能看见那群年轻的面孔。
而《等星星回家》的剧本也在稳步推进。他决定采用双线叙事:一条是五岁小月等待父亲归来的真实经历;另一条则是多年后已成为天文爱好者的她,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封未曾寄出的家书,由此揭开那段被岁月掩埋的情感。
剧本写到第三幕时,林晚带着小月来探班。小女孩一进门就扑向摄像机,好奇地东摸西看。王乐天笑着抱起她:“不怕机器吗?”
“不怕!”小月摇头,“这是讲故事的机器!”
林晚站在一旁微笑。她换了发型,穿一件浅蓝色毛衣,整个人显得柔和许多。两人对视一眼,都没有多说什么,但空气中似乎有什么悄然流动。
晚饭时,三人去了附近一家小餐馆。小月吃得满脸油光,忽然指着窗外一辆军绿色吉普车:“叔叔,那辆车好像爸爸以前开过的!”
王乐天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车子早已驶远。
“你记得爸爸的样子吗?”他轻声问。
小月歪头想了想:“记不太清了……但我记得他的声音。晚上睡觉前,他会打电话给我,说‘宝贝,爸爸在追星星呢’。他还说,等我把所有星星认全了,他就回来。”
林晚低头搅动碗里的汤,声音很轻:“他最后一次通话,是在发射前夜。他说任务特别重要,可能很久都不能联系家里。我让他别太拼,他说:‘这次要是成了,以后的孩子们就能用咱们的导航看世界了。’”
王乐天握紧筷子,喉头滚动。
“你知道吗?”林晚抬眼看他,“他一直收藏着你早期写的书。说你是少数能把普通人写活的作家。他还说过,希望有一天,你能写写我们这些人。”
王乐天怔住。
“我不是特意等你来写的。”他低声道,“我是走到今天,才终于看得见他们。”
饭后散步回工作室,路上经过一片居民区。夜色深沉,万家灯火。小月牵着两人的手,蹦蹦跳跳地唱着幼儿园学的儿歌。走到楼下时,她突然停下,指着天空:“快看!流星!”
两人抬头,只见一道银光划破夜幕,转瞬即逝。
“许愿了吗?”林晚笑着问。
小月认真点头:“我许愿爸爸变成的那颗星,永远亮着。”
王乐天望着天际残痕,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他知道,那一颗星或许从未存在,但它承载的信念,却比任何星辰都要恒久。
回到工作室,他打开电脑,新增了一段戏:
>【夜,天文馆穹顶】
>成年小月站在投影星空下,手中握着一封泛黄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