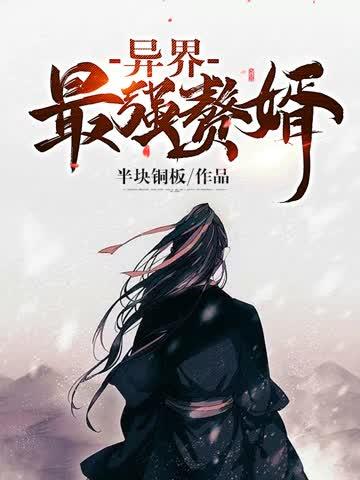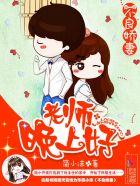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的一九八五 > 第一八四一章 反目成仇(第1页)
第一八四一章 反目成仇(第1页)
“张副院长,MountEverest的总设计师是不是布莱恩?胡克?”
3dfx有4位联合创始人,分别是斯科特?席勒斯、加里?塔罗利、罗斯?史密斯和戈登?坎贝尔,前三位都来自硅图公司(SGI)。。。。
阳光斜照进北京西城区一处老旧居民楼的阳台,几盆茉莉花开得正盛,香气混着楼下小摊煎饼的油烟味飘进屋里。孙健坐在窗边那张磨得发亮的木桌前,翻看刚打印出来的《听见者手记》校样稿。书稿已通过出版社终审,下个月就要付印。编辑在邮件里说:“这本书可能会改变很多人对‘声音’的理解。”
他笑了笑,把最后一段读了一遍又一遍。
就在这时,手机震动起来。是PENG后台的紧急通知:
>【突发情感危机预警】
>地点:黑龙江漠河市北极村教学点
>事件类型:群体性语言退化
>核心症状:五名儿童连续二十一天未使用完整句子交流,仅以单音节回应外界刺激
>关联背景:该教学点三年内已有两名教师因极寒与孤独辞职,现由一名代课老师兼任校长、厨师与心理辅导
孙健眉头紧锁。这不像龙潭寨那种物理隔绝,也不似韦小勇那样的个体创伤??这是缓慢的精神冻结,像冰层一寸寸覆盖水面,无声无息地吞噬语言的生命力。
他立刻拨通林妍电话:“准备设备,我们要去中国最北端。”
“又要走?”林妍的声音带着疲惫,“上个月你刚从云南回来,医生说你心律不齐,得休息。”
“可他们等不了。”孙健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不是不说,而是他们已经忘了‘想说’这件事本身。一旦语言死了,灵魂也就开始冬眠。”
三天后,他们踏上了前往漠河的旅程。飞机、火车、雪地摩托,最后徒步穿越一片被暴雪封锁的原始林区。零下三十八度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呼出的气息瞬间凝成白霜挂在睫毛上。当北极村那座孤零零的教学点出现在视野中时,整个村庄正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极光笼罩,绿色光带在夜空中缓缓流动,宛如神明低语。
教学点是一座低矮的木屋,屋顶压着厚厚的积雪,烟囱冒着微弱的青烟。门推开时,一股混合着煤炉味和旧毛衣潮湿气息的暖流扑面而来。那位代课老师姓陈,四十出头,脸上刻满风霜,见到他们只是点点头,没多说话。
教室里,五个孩子围坐在火炉旁,眼神呆滞,动作迟缓。听到脚步声,其中一个男孩轻轻“嗯”了一声,便再无反应。墙上贴着褪色的拼音表和一幅手绘地图,写着“我们的祖国”,角落里还挂着一个破旧的铃铛,据说是以前下课用的。
“他们不是哑巴。”陈老师低声说,“去年冬天还能唱歌,讲童话。但今年雪特别大,封山五十多天,快递断了,信没人寄,连广播都听不清。慢慢地……话就越说越少。”
孙健蹲下身,拿出便携录音机播放一段来自海南三亚某小学的声音:“喂!北极的小朋友,我们这儿沙滩可暖啦,海浪天天唱歌给你们听!”接着是一群孩子嘻嘻哈哈模仿海鸥叫的声音。
没有反应。
他又试了一段新疆喀什孩子们跳麦西来甫的节奏录音,鼓点欢快,歌声热烈。其中一个女孩手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要拍掌,却又停住。
林妍轻声问:“要不要试试‘喊魂曲’?”
孙健摇头:“这里不一样。龙潭寨的人是在等待回应,而他们是……已经不相信回应存在了。我们必须先让他们重新相信‘声音能抵达远方’。”
当晚,他们在屋顶架起定向声波发射器,并连接卫星通道,将教室变成一个临时的声音中继站。孙健设计了一个“回声计划”:让每个孩子对着麦克风说一个词,哪怕只是一个音节,系统会自动将其转化为一段旋律,发送到PENG平台,随即由AI生成一句来自其他地区孩子的回应,实时传回。
第一个尝试的是那个曾动过手指的女孩,名叫李萌。她盯着麦克风看了很久,终于小声说了两个字:“冷……灯。”
系统立刻处理并推送出去。
十分钟后,喇叭里传出一个稚嫩的声音:“姐姐,我不怕黑,因为我床头有星星灯!你要不要也有一盏?我让妈妈给你寄一个!”
李萌怔住了。她抬头看向孙健,嘴唇微微颤抖。
第二天,她主动走到麦克风前,说:“我想……看见花。”
这一次,回应来得更快。广州一位小女孩清脆地说:“我家阳台上开满了三角梅,红的、粉的,像火烧云!明年春天,我拍视频给你看!”
第三天,五个孩子轮流说话。有人说“想吃甜的”,立刻收到广西小朋友寄来的手工糖果配方;有人嘟囔“梦里有狗”,结果青海牧区的一个藏族男孩兴奋地回:“我家阿黄可听话了,它还会帮我找迷路的小羊!”
变化悄然发生。他们的语速变快了些,眼神开始聚焦,甚至会在听到有趣回应时笑出声。
但孙健知道,这些还不够。技术可以搭建桥梁,却无法替代真实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