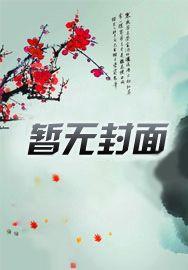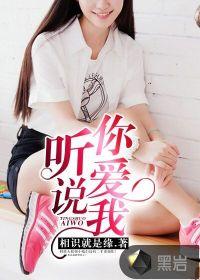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逍遥四公子 > 第1978章 痛并快乐着(第1页)
第1978章 痛并快乐着(第1页)
雪落无声,却在人心深处激起千层波澜。
那日之后,补言堂前的无名碑再未显现文字,铜镜也归于沉寂。可听城百姓知道,有些东西比显形更真实??它藏在清晨巷口一句“昨夜我梦见你娘了,她笑得很安详”,藏在私塾孩童交作业时主动划掉的虚假批语,藏在老吏翻出三十年前卷宗,颤声对遗孤说:“当年判你父亲死罪,是我篡改供词。”
语核井虽不再喷焰,但每逢雨夜,井壁仍会渗出淡蓝水珠,顺着石缝蜿蜒而下,如泪痕未干。村妇取此水煮茶,饮后常梦回少年,见自己未曾说出的真心;僧人以此水洗面,竟照见前世因果,痛哭三日不出禅房。有学者称其为“余音之露”,乃真言之力沉淀而成,非神迹,而是人心长期共振所凝。
这一年,南方大旱,江河断流,稻禾焦枯。朝廷开仓赈灾,派钦差巡视十郡。然而不过月余,便有流言四起:某县官虚报灾民人数以吞粮款,某漕吏勾结商贾倒卖官米,更有甚者,借“静言室”之名设局诱百姓自白家中藏粮,继而强征。百姓惶恐,渐渐闭口,连孩子也不敢再说“我饿”。
消息传至听城,皇帝未怒,亦未下令彻查。他只命人将一面铜镜从补言堂请出,置于宫门外百级台阶之上,镜面朝天,任风吹日晒。又诏告天下:“凡有冤者,可亲赴京城,立于镜前,说你想说的话。不必具名,不惧报复,若有一字虚妄,朕亲自下狱。”
起初无人敢信。第七日清晨,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农拄着枯枝走来。他跪在镜前,声音嘶哑:“我是桂阳县民,姓吴。去年我家六亩田全被征作‘皇粮试验地’,说种新稻能增产。可他们给的种子是假的……长出来全是空穗。我去找县令,他说我不懂农事,把我关了三天。后来我儿子去告状,路上摔下山崖……死了。”说到此处,老人伏地痛哭,“我不求升官发财,只求有人知道,我儿子不是白死的。”
话音落下,铜镜忽泛微光,竟将老人身影映得通透,仿佛体内有蓝丝游走。片刻后,镜面浮现一行小字:
>**吴氏吴德全,言出肺腑,心脉无蔽。**
次日,又有女子前来。她是阵亡边军之妻,丈夫战死后获赐“忠勇将军”谥号,却被族中叔父夺去抚恤田产,逼她改嫁。她站了整整一日,终于开口:“我说谎了。当年夫君出征前夜,我对他说‘你若不死,我就改嫁’,只为激他惜命。可他真的死了……我一直觉得,是我这句话害了他。”她泪如雨下,“我不是怨朝廷,我只是……想让他听见,我现在后悔了。”
镜光再起,浮字如前。
第三日,一名年轻书生到来。他曾因科举舞弊案被革去功名,多年来上访无门。他在镜前沉默良久,终道:“我确实贿赂过考官。但我之所以行贿,是因为主考大人先派人暗示,若不送银三百两,试卷必遭黜落。我不敢揭发,因为我爹病重,全家指望我一人翻身。”他苦笑,“我们都以为是我在腐化制度,其实是制度早已腐化了我们。”
这一回,镜中光影剧烈波动,竟持续整整半日才浮现铭文:
>**李文昭,罪中有苦,苦中尚存一念求真。可恕。**
自此,每日皆有人自四方而来。有贪官自陈受贿细节,附账册地图;有贵妇坦白毒杀庶子以保嫡位继承;甚至宫中老太监也悄然现身,低声讲述五十年前如何奉太后密令,用慢性药毁去先帝宠妃性命……每一句真话出口,铜镜便亮一分,最终整座京城夜间宛如白昼,光辉直冲云霄。
三个月后,皇帝亲率百官登阶,面对铜镜宣读《罪己诏》。他不提政绩,不论边功,只讲自己执政二十三年来的隐瞒与抉择:
“我曾为稳军心,隐瞒北境大败真相,致使三万将士家属迟迟不得抚恤;我曾在饥荒之年,强令地方上报‘仓廪充足’,只为避免邻国趁机犯境;我曾默许监察御史构陷政敌,因彼时权臣当道,不得不借污名除患……我知道这些谎言保住了江山,可我也知道,它们腐蚀了人心。”
他顿了顿,望向跪伏满地的臣子:“今日我在此立誓:自即日起,所有奏报不得有‘大致’‘约略’‘据说’之语。数据须精确到个位,事件须列明时间地点证人。若有欺瞒,不论品级,一律削职查办。宁可天下知我弱,不可天下信我伪。”
话毕,铜镜骤然碎裂,非外力所致,而是由内崩解,如冰融雪化。碎片落地即化为粉末,随风飘散,落入城中每一条街巷。当晚,全城百姓梦见一口巨大古井缓缓闭合,井口刻着八个字:
**真已生根,无需再唤。**
此后十年,大胤风气为之一变。官员议事不再避重就轻,百姓诉讼敢于直陈恩怨。最令人惊异的是,原本遍布各地的“静言室”竟逐渐消失??不是被拆除,而是自然湮灭。有人发现,只要屋内有人准备说谎,墙壁便会渗出蓝色水珠,气味刺鼻如腐锈;若诚心吐露,则空气清新似春林初雪。久而久之,人们宁愿露天相对,也不愿踏入那些“会呼吸的房子”。
与此同时,海外诸国纷纷遣使来学。高丽使者回国后设立“实语院”,要求贵族每日记录言行得失;波斯商人引入“心秤制度”,交易前双方须先声明是否有隐瞒动机;就连一向封闭的东瀛幕府,也在京都建起第一座“言省阁”,允许平民匿名投书揭发官吏恶行。
唯有西域某小国依旧抗拒。其君主宣称:“国民皆善,何须自剖?尔等所谓真言,不过是挑动内乱的妖术!”结果三年后国内爆发叛乱,起因竟是王储幼时误杀仆童之事被隐瞒多年,死者亲属代代相传仇恨,终酿血案。新君登基后痛定思痛,派人远赴听城求取陶片残铭,并在王宫之下挖井九丈,仿造语核井形制,却始终不得其法。直到一位盲眼工匠提议:“或许不是土木之工的问题,而是你们从未真正想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