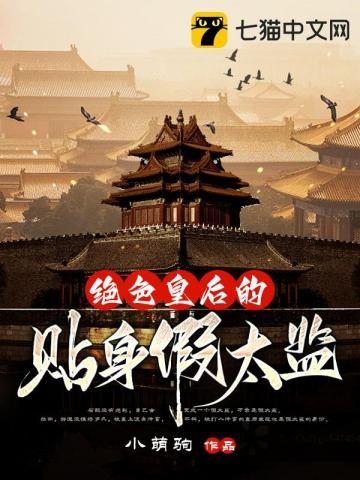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离婚后她惊艳了世界 > 第3074章 沈天予474盛魄(第2页)
第3074章 沈天予474盛魄(第2页)
空气骤然安静。
林知遥缓缓解开衬衫领口的第一颗扣子,将监测贴片贴在左胸位置。设备启动,心电图开始跳动。屏幕上,她的α波与θ波交织成独特的韵律,如同一首无人听懂的夜曲。
三分钟后,系统认证通过。
新的信息浮现:
>“知遥:
>如果是你打开了这封信,说明你还在为所有人背负重量。
>别这样。我不是神迹,也不是救世主。我只是个没能陪你走到最后的男人。
>你说你要学会爱一个不能触碰的人,可我想告诉你??真正的告别,是从不再愧疚开始的。
>你不必替我守护这个世界,也不必替我照顾他们。
>你只需要,好好地、自由地,做你自己。
>当你觉得足够幸福的时候,就是我能安心消失的时刻。
>P。S。那杯蜂蜜水,我一直记得温度。38。6℃,不多不少,正好是你说‘我爱你’那天早晨的体温。”
泪水无声滑落,滴在控制台上,溅起一圈微不可见的涟漪。
她忽然明白,他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消亡,而是被执念囚禁。他宁愿自己化作尘埃,也不愿成为她心中永远无法填补的空洞。
“关闭系统吧。”她轻声说。
小周犹豫:“可是……万一以后还有紧急情况?”
“那就让它再等等。”她望着那枚沉睡的存储芯,“有些话,一生只能听一次。听完了,就得学会自己走路。”
走出“永恒回廊”时,阳光正洒满花园。远处,禾宁带着小舟在围栏外放风筝,孩子笑得像个太阳。沈砚坐在长椅上看书,偶尔抬头望一眼花海,嘴角微扬。一切平静得仿佛从未有过奇迹。
林知遥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最顶端的名字,停顿片刻,按下拨号。
铃声响了两下,接通了。
“喂,知遥?”是程岩,前联合国科学顾问,现“回声工程”监督委员会主席,“这么早,有事?”
“我想申请辞职。”她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真的考虑好了?你是唯一能与Gaia-1产生深层共鸣的人。”
“正因为如此,我才必须走。”她望着天空中飘荡的风筝线,“有些光,照得太久会灼伤眼睛。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去一个没有Sorrowbloom的地方。”
“你想去哪儿?”
她笑了笑:“云南。听说那边有个小镇,四季如春,种满了普通的玫瑰和茉莉。当地人不知道什么是‘归音’,也不知道谁曾试图复活死者。”
“然后呢?”
“然后……我想开一家小小的书店。”她声音轻下来,“只卖诗集和童话。也许某天,我会写下我们的故事??不是作为科研案例,而是当作一本给孩子的睡前书。”
程岩叹了口气:“你知道吗?上周有个小女孩寄来一封信,说她梦见爸爸牵她去看星星,醒来枕头湿了一大片。她妈妈哭着问我们,能不能让孩子再多见一次父亲。”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也许真正的重逢,是在梦醒之后,依然能笑着说出他的名字。’”
林知遥闭上眼,风吹起她的发丝。
“告诉她妈妈,”她轻声道,“下次泡蜂蜜水的时候,多加半勺糖。他喜欢甜一点。”
挂断电话后,她沿着花园小径慢慢走着,直到站定在那块石碑前。指尖轻轻抚过“思念有界,爱无疆”几个字,像是在触摸一段终将沉淀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