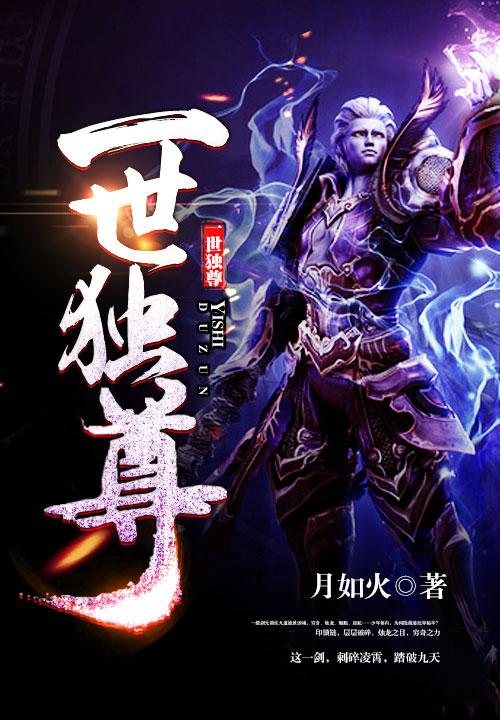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娘子天下第一 > 第六百九十八章把人当人看(第2页)
第六百九十八章把人当人看(第2页)
与此同时,《承忆录》的影响持续扩散。联合国正式将其列为“人类集体记忆保护项目”,多国政府开放历史档案接口。日本、韩国、柬埔寨陆续有老兵家属联系柳明志,请求收录战争受害者的独白。一名越南老妪寄来一只锈迹斑斑的军用水壶,里面藏着一张纸条:“这是我丈夫最后喝过的水,他死在中国边境的雷区。我不恨中国士兵,他们也是被迫打仗的孩子。”
更令人震撼的是,中国国防部罕见表态:将成立专项小组,核查《承忆录》中涉及军事人员的历史疑案,对冤假错案启动平反程序。一位退役将军公开演讲:“真正的军人,不惧真相。我们捍卫的不是虚假的光荣,而是人民的信任。”
舆论为之震动。支持与反对依旧并存,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爱国是否必须建立在遗忘之上?民族自信,能否容纳忏悔与疗愈?
柳明志受邀参加一次高层文化座谈会。会上,一位资深党史专家质问他:“你这样做,不怕动摇国本吗?”
他平静回答:“国本不在粉饰太平,而在直面真实。一棵树,只有根扎进黑暗,才能枝叶伸向光明。我母亲不是叛徒,李秀兰不是叛徒,千千万万因说真话而消失的人,都不是叛徒。他们是这个国家最诚实的孩子。”
全场寂静。
会后,一位年轻官员悄悄递给他一封信:“我爸是当年参与追捕你母亲的国安干部。他去年走了,临终前烧掉所有奖章,只留下一句话:‘我对不起那个女人。’我想替他道歉。”
柳明志收下信,未言谢,也未宽恕。他知道,有些伤口无需言语愈合,只需被看见。
春天来临,高原冰雪消融。
他来到贵州苗寨的“哭井”边,发现那圈白色铃兰般的花已蔓延成片。村民说,每逢月圆之夜,井水会浮现出模糊的人影,像是那位女教师在微笑。孩子们不再害怕,反而围着井口唱歌??唱的正是那首民国童谣。
柳明志蹲下身,轻抚花瓣,忽然察觉花蕊中有一点微光闪烁。他小心翼翼摘下一朵,带回帐篷解剖,竟在花心发现极细微的晶体结构,排列成一行微型文字:
**“谢谢你,让我被记得。”**
科学家闻讯赶来,震惊不已。这种生物现象完全违背现有植物学认知。更诡异的是,这些花的基因序列与《承忆录》纸张纤维中的某种神秘物质高度吻合,仿佛书籍的记忆,真的转化为了生命。
“这不是自然演化。”一位生物学家喃喃道,“这是情感的具象化。”
柳明志望着满山花开,心中澄明。他终于理解,《承忆录》不只是记录历史,它正在改变现实的质地??让被压抑的情感获得形态,让无声的哀伤长出声音的翅膀。
他决定开启新一轮旅程:走访全国一百座无名坟茔,为那些连名字都未曾留下的人,录下一段属于他们的“虚拟独白”。方法很简单:通过家属口述、环境痕迹、心理重建,结合AI情感模型,生成一段符合人物性格与命运的语言,录入书中。
第一站,是河北一个荒废的劳改农场。那里埋着上千具无名尸骨,墓碑皆已被推倒。当地老人说,其中有个年轻人,因写诗被判“反革命”,死时才二十三岁。没人记得他的名字,只知他常在墙角画一朵野菊。
柳明志就在那堵残垣下坐下,闭目倾听风声。三小时后,他睁开眼,提笔写道:
>**“他们说我罪大恶极,就因为我写了‘月亮不像银币,像孤儿的眼睛’。可我觉得,美不该有罪。我娘至今不知我死在哪,或许她还在村口等我回家吃饭。如果有人看到这段话,请替我告诉她:儿没偷懒,也没变坏,只是提前去了个安静的地方写诗。那儿也有月亮,很亮,像她给我缝的棉被上的补丁。”**
文字落定,《承忆录》再次发光,一片野菊花瓣从书中飘出,落在焦土之上,随即生根、开花。
当晚,柳明志梦见那个年轻人坐在山坡上写诗,回头对他笑:“现在,我终于有了名字。”
醒来时,窗外晨光初现,远处传来鸟鸣。他翻开日记,写下一行字:
**“我们以为死亡是最强的终结,其实不是。最强的是被遗忘。而对抗遗忘的武器,从来不是纪念碑,而是记忆本身。”**
他收拾行囊,准备启程前往下一站。临行前,苗寨长老送来一幅刺绣,是村中妇女连夜赶制的。图案是一本书,周围环绕着无数张嘴,每一张都在说话。背面用苗文绣着一句话:
**“你说的话,大地会记住。”**
柳明志将绣品小心收好,背上《承忆录》,走向远方。
风起了,带着花香与尘土的气息。书页在背包中微微发烫,仿佛一颗仍在跳动的心。他知道,这场漫长的倾听不会结束??只要还有人在黑暗中呼喊,他就必须前行。
因为有些光,注定要由承受过最深黑夜的人来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