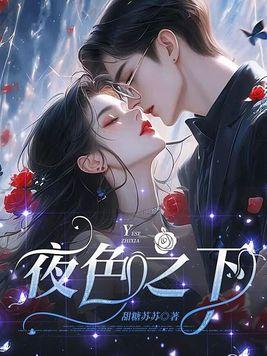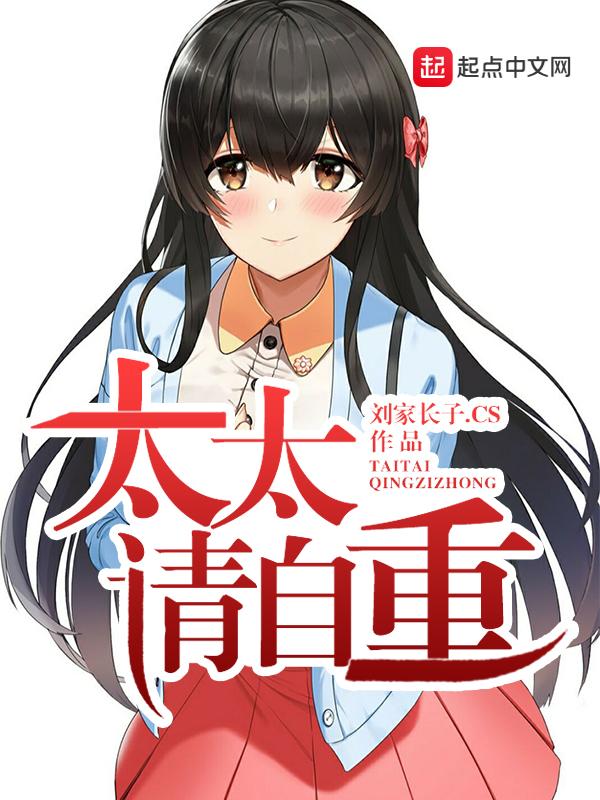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外科教父 > 1254章 乡愁(第3页)
1254章 乡愁(第3页)
老人的眼神渐渐飘远,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阻隔。
“光绪二十三年,我们的曾祖父背着一个小小的行囊,在厦门港登上了开往槟城的货船。临行前,他跪在村口的榕树下,捧起一把黄土装进香囊。“郭敬尧的声音微微发颤,“那时他说:此去南洋,若得温饱,必返故乡。”
然而,这个承诺,一等就是几代人。
郭敬尧缓缓踱步到墙边,掀开一幅丝绸遮盖的地图。那是一张手绘的南洋华人支援抗战的路线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捐款渠道、物资转运站。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电报传到槟城时,祖父正在为新的橡胶园剪彩。”老人的手指轻抚着地图,“他当场撕碎了贺词,登上讲台高呼:华夏危急!”
“那时的南洋华人,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援华浪潮。街头巷尾,卖云吞面的小贩捐出每天收入的一半;橡胶园里的割胶工,将积攒了半年的工钱悉数献出。祖父更是变卖了三处产业,通过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
国难民总会”,将整整十辆卡车的药品送往西南大后方。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黄包车夫。“郭敬尧的眼眶微微发红,“他每天拉着车在槟城的大街小巷穿梭,收工后总会来到我们家门口,从怀里掏出一个还带着体温的铜板。”
“1942年,日军铁蹄踏遍马来半岛,祖父因为积极援华而被列入通缉名单。全家被迫逃往丛林深处的种植园避难。即便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祖父依然在茅草屋中坚持教导子女读《三字经》、写汉字。”
“临终前,祖父把我叫到床前,交给我一把钥匙。“郭敬尧走向保险柜,取出一本已经发黄脆化的账本,“这是郭家所有的海外资产记录。他说:这些产业,终有一日要用于报效祖国。
会议室里寂静无声,连最浮躁的年轻一代也都屏住了呼吸。
郭敬尧的声音开始哽咽:“八十年代,当我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回到福建老家时,带着的是祖父的遗像。我在那个已经破败的祖宅前,跪了整整一个下午。”
他打开投影仪,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老照片:一个瘦小的男孩站在槟城的码头,眺望着西北方向的海平面。
“这是1939年的我。“郭敬尧轻声说,“那时我每天都会去码头,因为大人们说,从那里一直往北,就能回到中国。”
长久的沉默在会议室里蔓延。窗外,南洋的晚霞正如火如荼地燃烧着,将整个天空染成一片红色。
“现在,“郭敬尧缓缓站起身,目光如炬,“祖国需要突破科技壁垒,需要实现产业升级。那些西方人,以为还能像一百年前那样用枪炮让我们低头吗?不!这一次,我们要用智慧、用毅力,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双手,打破这
道无形的墙!”
他重重地拍在桌面上,震得那盆水仙微微颤动。
“我决定,首批投入一百亿美金成立破壁基金。同时,在全球设立六个人才招募中心,用最好的条件,请回最顶尖的华人科学家。”
“父亲!“次子修武忍不住站起来,“这几乎是我们流动资金的五成!集团正在进行的几个重大项目都会受到影响!”
“那就暂停!”老人的声音不容置疑,“修武,你记住,钱可以再赚,但民族的机遇,稍纵即逝。”
郭敬尧重新走回主位,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微微前倾:
“孩子们,我们郭家在南洋奋斗了四代,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但这些财富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是让我们过上多么奢华的生活,而在于当历史再次来到十字路口时,我们有能力为民族,为祖国做出一点贡献。”
他的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投向那片被晚霞浸染的天空,声音忽然变得轻柔:
“曾祖父离乡时带走的那个香囊,我一直珍藏着。里面的泥土已经快要流失殆尽,但那份对故土的眷恋,却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让这棵漂泊了百年的相思树,把根系重新扎回祖国的土壤。”
泪水,终于从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眼中滑落,滴在泛黄的账本上,晕开了一百年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