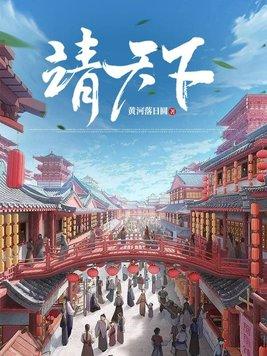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都重生了谁考公务员啊 > 第708章新年伊始简在帝心(第1页)
第708章新年伊始简在帝心(第1页)
子鼠随冬去,金牛踏春来!
这一年春节假期过的也很快,其实对陈着来说,本应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只是因为格格的贸然来访,险些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幸好,没出什么太大问题!
年初五的时候,。。。
夜深了,陈着却还没走。
办公室的灯一盏接一盏熄灭,只剩他这间还亮着。窗外城市灯火如星河铺展,远处高架桥上的车流像一条缓缓流动的光带。他靠在椅背上,手里捏着一张照片??是上周云南支教团传回来的:一群孩子蹲在泥地上,围着一台“共学盒”,屏幕微光映在他们脸上,像是某种古老的仪式。有个小女孩正用铅笔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写着什么,镜头拉近才看清,她写的是:“我要当法官。”
他把照片夹进笔记本,合上电脑,正准备离开,手机突然震动。是一条系统警报:**“回声通道”检测到异常高频关键词??“土地确权”“征地补偿标准”“集体资产分配”**,触发区域集中在湖南、江西、安徽三省交界地带,涉及用户超过一万两千人,且72小时内咨询量增长460%。
他皱眉点开详情,发现这些请求大多来自同一个源头:一个名为“皖南共学小组”的民间学习群。他们在平台上自发组织了“法律互助会”,每周轮流主持讨论,最近一次的主题是《农村妇女如何主张宅基地权利》。有人上传了一份录音,是一位村干部在村民大会上说:“女人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哪还能分地?”紧接着,群里立刻有人贴出《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八条的节选,并附上一段语音讲解:“这不是讲理,是违法。”
陈着盯着那条语音转文字的内容看了很久。声音很轻,带着浓重方言口音,但每个字都咬得极稳:“我叫吴秀英,四十九岁,小学没毕业。去年学完‘婚姻家庭课’,我去乡政府问了我的名字有没有登记在土地承包合同上。他们说没有。我说我要查档案。他们笑了。我说笑归笑,我要复印材料。他们不给。我就坐在窗口不走,从早上八点坐到下午五点。最后给了。我发现合同上只有我老公的名字。我拿着法条去理论,他们说‘村里历来就这样’。我说,历来这样,不代表合法。我现在已经在准备起诉了。”
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无数个这样的场景:不是演讲台上的慷慨激昂,而是灶台边低声翻书的母亲;不是法庭上的唇枪舌剑,而是村委会门口久久不愿离去的身影。
他知道,这已经不再是“教育”能涵盖的事了。
第二天清晨,他在会议室召集团队紧急开会。林小雨带来最新数据:“过去一个月,平台‘法律类’课程日均访问量突破百万,其中‘征地维权’‘集体经济分红’‘离婚财产分割’三类课程完课率最高,平均达89。2%。更关键的是,用户开始主动上传案例、整理模板、互帮互助,形成了至少三百多个区域性‘共学+行动’社群。”
“我们正在成为某种……替代性公共系统。”她说,“人们不来找政府,先来问‘共学’。”
会议室一片沉默。
财务总监迟疑道:“可我们没有律师团队,也没有调解资质。万一有人依我们课程里的内容去闹事,出了问题谁负责?”
“他们不是‘闹事’。”陈着声音平静,“他们是第一次知道,自己有权利说话。”
他站起身,走到白板前写下四个字:**知行合一**。
“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知’落地成‘行’。如果一个人学了法律却不敢用,那这门课就是失败的。但如果她用了,却被当成麻烦制造者,那这个社会才是失败的。”
顿了顿,他说:“联系司法部合作团队,请他们协助我们上线‘基层法律实践指南’专题。同时启动‘共学援助计划’:招募五百名公益律师,组成线上志愿团,为用户提供免费初步咨询。每台‘共学盒’增加一键求助功能,接入当地法律援助中心热线。”
林小雨忍不住问:“这会不会太激进?我们毕竟不是NGO,也不是政府部门。”
“那就做第一个既不是NGO也不是政府,却能让普通人活得更有尊严的企业。”陈着看着她,“你说过,用户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知识。那我们就陪他们走下去??哪怕这条路通向风暴中心。”
项目启动第三天,第一起事件爆发。
湖南醴陵一位名叫周玉梅的农妇,在完成“土地权益课”后,向村委会申请查阅村集体资产台账,遭拒后当场播放《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音频,并声明将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村干部报警称其“扰乱公共秩序”,警察到场调解时,她掏出打印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复印件递上去:“我不吵不闹,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全村三百亩流转土地的补偿款名单里,没有一个女人的名字?”
视频被同村人发上网,短短半天转发超二十万。有网友评论:“原来最硬核的维权,是一个农村妇女背法条的样子。”
与此同时,压力再度袭来。
某省级主管部门约谈平台驻地办事处,明确表示:“鼓励学习,但反对借知识之名煽动对立。”更有媒体撰文质疑:“民间普法是否正在演变为基层对抗的导火索?”甚至有地方教育局通知学校,禁止学生带“共学盒”回家,理由是“内容未经属地审查”。
陈着没有回应。
他只做了一件事:将周玉梅的完整经历制作成纪实短片《她读法典那天》,由平台官方账号发布。片中没有任何煽情旁白,只有她一字一句朗读《民法典》的画面,穿插她在田埂上填写行政复议申请表的手部特写,以及她女儿在一旁默默抄写“妈妈说,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日记片段。
视频结尾,是一段采访:
记者问:“你怕吗?”
她摇头:“怕啊。但我更怕我女儿以后也被人说‘女娃不用懂这些’。”
发布不到十二小时,#她读法典那天#登上热搜榜首。全国妇联官微转发并配文:“每一个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的女人,都是时代的光。”最高人民法院公众号随后推出专题《从田间到法庭:那些正在改变中国的女性》,引用该案作为“法治下沉”的典型案例。
风向悄然逆转。
一周后,中央政法委官网刊发评论文章《让法律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明确提出:“推动全民守法,不仅要普及条文,更要支持群众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任何阻碍普通人知法、懂法、用法的行为,本质上是在削弱法治根基。”
政策松动的同时,变化也在野蛮生长。
四川大凉山深处,一个由十二名彝族妇女组成的“阿嫫共学组”(阿嫫意为母亲),利用平台学到的合作社注册流程和电商运营知识,创办了“云端羊毛坊”。她们将自家羊群剪下的羊毛手工纺线、染色、编织成民族风围巾,通过直播销售。最关键的是,她们坚持所有交易使用成员个人账户,拒绝由男性亲属代管资金。
“以前卖羊,钱直接打给男人。”组长阿呷在一次连线分享中说,“现在我们卖的是手艺,是我们的时间和心血。凭什么不能自己收?”
类似的故事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