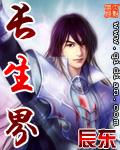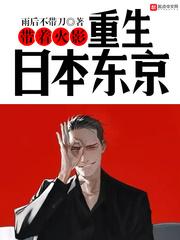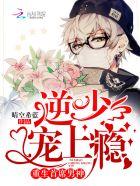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都重生了谁考公务员啊 > 第701章格格要登门(第2页)
第701章格格要登门(第2页)
一周后,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态:“政府始终鼓励和支持群众性、公益性的学习互助活动。对于实践中出现的新形态,应以包容审慎的态度加以引导,而非简单禁止。”同时宣布将在下半年开展“全民终身学习推进行动”,明确提出“推广共学伙伴经验,建设一万五千个城乡社区学习站”。
政策闸门悄然打开。
七月流火,平台迎来历史性时刻:注册用户突破八千万,累计促成共学结对超过一百三十万次。与此同时,“共学伙伴”模式已被复制到海外华人社区,并开始尝试进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帮助当地失学青年重建学习路径。
但在所有成就中,最让陈着动容的,是一个来自广西百色的电话。
打电话的是位七十多岁的退休语文教师,姓韦。她说自己看了报道后,决定回到老家屯里,把她家的老屋腾出来办“乡村读书角”。她一个人买了黑板、课桌、几十本拼音读物,又说服两个孙子周末回来帮忙教学。“现在有十七个孩子来上课,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才六岁。他们叫我‘阿婆老师’。”她的声音沙哑却坚定,“我教了一辈子正规学生,临老了才发现,最有成就感的课,是在自家堂屋里上的。”
她最后说:“陈老师,谢谢你让我知道,退休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开始。”
挂掉电话那天,北京下了场大雨。
雨水顺着窗户蜿蜒而下,像无数条奔流的小河。陈着坐在办公室,翻看近期各地传来的简报:内蒙古科尔沁旗成立首个“牧民共学联盟”,成员全是五十岁以上的放牧老人,他们白天放牛,晚上聚在蒙古包里轮流朗读报纸;江苏南通一家养老院引入“代际共学”项目,让老年人教小学生方言童谣,孩子们反过来教老人用微信视频通话;更有意思的是,连一些高校研究生也开始参与进来??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几名硕士生自发组织“田野共学团”,深入云南边境村落,一边调研一边担任线上助教,甚至还帮当地妇女设计出一套“傣语-汉语双语识字卡”。
这个世界正在悄悄改变。
不再是单向施舍,不再是居高临下的拯救,而是一种平等的流动:你教我认字,我教你种菜;你帮我理解政策,我陪你走过孤独。知识不再囤积于象牙塔,而是化作涓滴细流,渗入每一道干涸的裂缝。
八月初,陈着接到通知:平台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创新典型案例库”,并将代表中国参加年底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学习型社会峰会。
林小雨开玩笑说:“你要成国际名人了。”
他摇头:“我只是个见证者。真正该站上讲台的,是张守田、是赵小雨、是周大山、是千千万万不肯向命运低头的普通人。”
出发前夜,他再次打开数据库,调出最新数据画像。
屏幕上跳出一组数字:
-累计完成初阶语文课程人数:**96。7万人**
-其中女性占比:**53%**
-四十五岁以上群体:**62。1%**
-通过学习实现收入增长或就业转化者:**逾28万人**
他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过去半年中,平台收到的感谢信数量呈指数级上升,而这些信件的内容也在悄然变化??早期大多是“谢谢你们让我学会写名字”,如今越来越多变成“我帮邻居打赢了土地纠纷案”“我女儿说我讲的故事比电视里还好听”“我现在敢在村民大会上举手发言了”。
原来,识字真的不只是为了阅读。
是为了发声,是为了站立,是为了在漫长的人生中途,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名字。
巴黎峰会当天,会场座无虚席。各国代表围绕“数字时代的教育公平”展开讨论。轮到陈着发言时,他没有展示PPT,也没有引用统计数据,只是播放了一段五分钟的视频。
画面里,有凌晨五点亮起的灶火,有羊圈旁滑动手机屏幕的小手,有老农拿着扶贫公示表逐字核对的身影,有服刑人员颤抖着念完一封家书的瞬间,有一个个孩子仰着脸喊“马校长”的笑脸……
视频结束,全场静默十秒,随后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一位非洲代表站起来说:“在我的国家,很多人以为改变必须从首都开始。今天我才明白,有时候,真正的变革,始于一个女人在厨房里教会女儿读第一句话。”
回国后,他又一次走进那个熟悉的数据库后台。这一次,他新建了一个标签,名为:“已看见”。
他把所有那些写下“我敢抬头了”“我终于像个明白人”“我也能帮别人”的用户,都归入其中。
截至当日,总数已达**412,856人**。
他知道,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
就像春天的野草,无人播种,却自有方向;看似柔弱,却能掀开压在头顶的石板。
某日黄昏,他路过一所小学门口,听见几个孩子叽叽喳喳地讨论作业。
“你说,什么叫‘改写未来’啊?”一个小男孩问。
旁边女孩抢答:“就是你现在学的东西,以后能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呗!”
他驻足片刻,嘴角微微扬起。
然后掏出手机,在朋友圈发了一张街景照片,配文仍是那句:
>“今天,中国有九十六万个‘张守田’站了起来。
>他们不是要改变世界,只是想堂堂正正地说一句:我知道我在哪,我要去哪。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