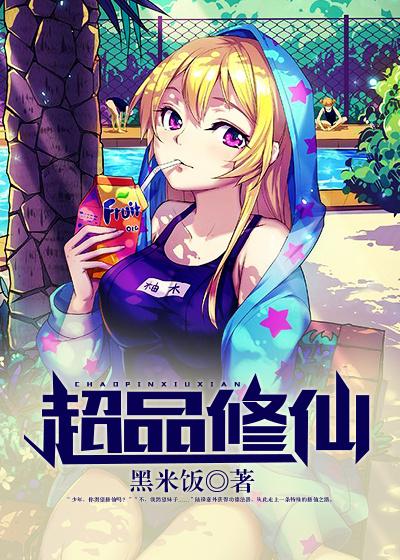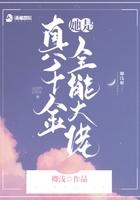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在现代留过学 > 第一千零八十二章 直把谅州作汴州(第2页)
第一千零八十二章 直把谅州作汴州(第2页)
“我们是否该采用官方修史体例?”一位白发老儒问道,“纪传体可立人物,编年体可明时序,方志体则便于地方流传。”
“不可!”一名年轻女子站起,她是江西来的陈氏女,父亲因私撰《赣东实录》被杖毙,“庙堂之史,重权贵而轻黎庶。我们要写的,是百姓自己的历史。当以口述为主,辅以实物凭证,按‘事?人?地’分类,每一条记录必注明出处与见证人。”
众人议论纷纷。阿禾静听良久,终于起身:“诸位,我们不是在模仿朝廷修史,而是在重建一种记忆的权利。因此,不必拘泥古法。我建议设立‘三真原则’:真名、真事、真证。凡收录者,必须具名作者,注明采录时间地点,若有物证,则附拓片或绘图。宁缺毋滥。”
他又道:“其次,每省所辑,不限一册。可分《灾异录》《冤狱志》《劳役簿》《童谣集》《葬歌谱》等类,务使各类人群皆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声音。”
此议一出,众人皆服。
会议持续半月,终定《民史共录会章程》十二条,其中第九条尤为严苛:“凡篡改、隐匿、销毁他人史录者,视为背叛全体执笔者,永除名籍,天下共讨之。”
清明当日,众人登岳麓山,在一棵千年银杏下举行“血书立誓”仪式。每人以针刺指,滴血入酒,共饮盟誓。随后将首批《楚南痛史》抄本密封入石龛,埋于树根之下,并立碑曰:“待百年后启封,看今人如何面对真相。”
阿禾亲手刻下碑文,最后一笔落下时,忽觉胸口铜铃一震。
他猛然回头,只见山道尽头奔来一人,衣衫破碎,满脸血污,正是此前派往北直隶查访“北井断”真相的川井七副手。那人扑倒在碑前,嘶声道:“京师……出大事了!”
原来,甘兰进虽已被斩首示众,其女甘玉瑶却趁乱逃脱,潜入宫中,竟以先帝宠妃侄女身份冒充宫人,勾结残余宦官,暗中策动一场“正史净化运动”。她联合礼部侍郎周允文,假借整理档案之名,系统性焚毁涉及忆堂旧案的所有原始卷宗,并散布谣言,称阿禾等人所录皆为“妖言惑众”,欲图谋反。
更令人震惊的是,皇帝近来沉迷丹药,神志昏聩,竟准许周允文成立“国史澄清司”,下令全国搜缴《未删国史》及一切野史抄本,违者以“大不敬”论罪。已有十余名执笔者被捕,三座主坛遭毁。
“苏井三!”那人紧抓阿禾衣袖,“他们说您是逆首,悬赏千金取您人头!”
堂中一片死寂。
片刻后,陈氏女冷笑一声:“他们烧得了纸,烧不了人心。”
阿禾缓缓站起,目光扫过众人:“既然他们要打碎我们的笔,那就让我们用骨头写字;既然他们要堵住我们的嘴,那就让大地替我们发声。”
他当即下令:南方七井转入地下,所有活动改为夜间进行;各地加速培训传声童子,重点教授记忆法与密写术;同时启动“星火计划”??将重要史料缩写成童谣、谚语、戏文,在市井广为传唱。
他自己则决定重返京城。
“我去会会这个甘玉瑶。”他说,“有些账,该当面算清楚。”
入冬之前,阿禾乔装成卖炭翁,混入京畿。他借宿在一座废弃尼庵,与一名曾为忆堂抄录员的老尼相依为命。夜夜伏案,将十年来收集的证据重新梳理,尤其聚焦甘家三代贪腐脉络:从甘兰进虚报军功,到其父甘承业在万历年间操纵科举舞弊,再到甘玉瑶幼时便参与销毁账册的蛛丝马迹。
他写出《甘氏三世奸实录》,全文一万三千言,引证八十七处,附图六幅,其中包括一张由福建盐贩提供的走私航线图,以及一份甘府家奴口述的“灭口名单”。
腊月初八,京城大雪。
阿禾将这份文书誊抄七份,分别藏于七个不同渠道:一名赴考举人的琴盒夹层、一位走镖武师的刀鞘内壁、一个街头说书人的鼓肚之中……最冒险的一份,他亲自送入国子监某位良心未泯的助教手中,嘱其若遇不测,便在讲经时朗声诵读。
七日后,奇变陡生。
那位说书人在天桥茶馆表演新编评书《忠义井》,讲述泉州火灾真相,听众数百,无不泪下。巡城御史带人抓捕,说书人当场吞纸自尽,临死前高呼:“我记得!”与此同时,国子监助教果然在课堂上宣读《甘氏实录》,引发学生哗然,三百学子集体跪谏,请皇帝收回“澄清司”成命。
风浪席卷全城。
甘玉瑶大怒,命周允文调兵围捕,一夜之间抓走七十余人。然而她万万没想到,就在审讯最严酷之时,宫中忽然传出消息??皇帝服丹暴毙!
乱局骤起。
太子尚未登基,内阁紧急议政。关键时刻,一名老太监捧出一只铁匣,声称是先帝临终前密藏于佛龛之后,内有一道未曾公布的遗诏:“朕知甘氏弄权久矣,然碍于旧勋,迟迟未决。今观野史累累,民怨滔滔,若再掩耳盗铃,恐江山动摇。特令新君重启忆堂案,彻查甘党余孽,赦免所有民间录史之人,赐‘直言之士’匾额一方,永享免税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