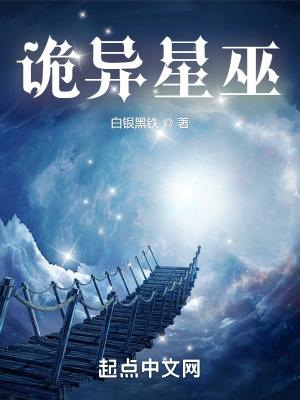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隆万盛世 > 1587战场(第3页)
1587战场(第3页)
朝廷再度震动。疑政院残余势力联合大理寺上奏,请求派兵封锁洱海,缉拿“聚众惑民”之徒。然而奏章递入宫中,却迟迟未批。原来皇帝自那夜梦见孩童质问后,精神日渐恍惚,常独坐殿中自语:“朕真的听见了吗?还是只是梦?”太医束手无策,唯有御前侍读悄悄禀报:陛下近来每夜必读《贞观政要》,尤其反复翻看“纳谏篇”。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问答墙”数量突破千面。更有奇者,有人将问题刻于风筝之上,放飞天际;有渔夫在船帆上绣满疑问;边疆哨所的士兵用雪堆出巨大文字,航拍可见:“我们为何而战?”
而在京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一座废弃戏台被人悄然改造。台上无戏文,只悬一块黑板,每日清晨由匿名者更新一句话。某日清晨,万人驻足,只见黑板上赫然写着:
>“阿菱不是领袖,问题才是。”
下方,有人用粉笔添了一句:
>“那么,请问:谁赋予领袖权力,又由谁来监督权力?”
这一问,如星火落于干草。当晚,国子监数十名学子集会,联名上书,要求重开“议政课”,恢复宋代“廷辩制”。军营中,年轻军官私下传阅一本手抄册子,名为《兵问录》,首篇即问:“若将军令违民心,士兵当忠于令,还是忠于民?”
风暴已成,无可遏制。
阿菱得知这些时,正行至长江北岸。她站在渡口,望着滚滚东去的江水,忽然对沈知意说:“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
“为什么?”沈知意愕然。
“因为我们已经不需要到达某个地方。”阿菱微笑,“问题本身,就是目的地。”
她取出炭笔,在岸边一块巨石上写下:
>“不要等待救世主。
>你提出问题的那一刻,
>你就是光。”
写毕,她将笔扔入江中。笔随水流漂远,像一支射向未来的箭。
当晚,她做了一个梦。
梦中,她回到南岭石室,铜铃依旧悬挂,但铃舌已不见。她抬头,看见无数人站在世界各地的墙前、碑旁、树下、舟上,同时开口提问。千万个声音汇成一股洪流,直冲云霄。那股力量穿透地壳,撼动洱海深处。漆黑海底,淤泥翻涌,一只巨大的青铜铃缓缓升起,铃舌晶莹,正是她水晶瓶中醒梦花结晶所化。
两铃遥相对望。
然后,同时震动。
没有声音,却让整个大地为之战栗。
她惊醒时,窗外正电闪雷鸣。雨点砸在屋顶,如同万千手指敲击鼓面。她起身推窗,见沈知意也已站立院中,仰头望天。
“你也梦见了?”沈知意问。
阿菱点头。
两人相视而笑。
就在此时,远处山巅,一道闪电劈落。光亮刹那照亮天际,仿佛天地之间,有一口无形的大钟被猛然叩响。
叮??
那一声,不在耳中,而在心上。
而在千里之外的皇宫,皇帝猛然从榻上坐起。他没有叫太监,没有点灯,只是呆坐黑暗中,嘴唇微动,仿佛在回应某个无人听见的提问。
良久,他低声自语:
“也许……朕该去问问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