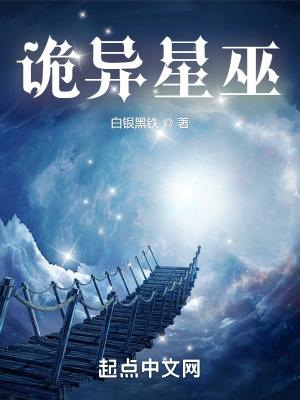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隆万盛世 > 1587战场(第2页)
1587战场(第2页)
>3。若无人能答,问题将被抄录送往其他“问源站”。
>4。所有问题,皆视为火种,不得熄灭。
次日清晨,阿菱独自走出校舍,来到村外一片荒坡。她从怀中取出那只空了的水晶瓶,对着朝阳举起。瓶底最后一丝银芒在阳光下闪烁了一下,随即彻底消散。她轻轻将瓶子埋入土中,低语:“谢谢你,带我醒来。”
返程途中,她们途经一座废弃驿站。驿站门廊坍塌,梁柱倾斜,唯有正厅尚存。推门而入时,一股陈年尘气扑面而来。厅内蛛网密布,地面积灰寸许。然而,在正对大门的墙壁上,竟有一片区域异常干净,仿佛recently被人擦拭过。
墙上贴着一张黄纸,墨迹犹新:
>“阿菱:
>你走之后,腾冲来了官差,查问‘问答墙’之事。村民起初恐惧,无人应声。后来那个叫阿?的小女孩站出来,指着墙上的字说:‘这是我写的,怎么了?’官差怒斥她妖言惑众,要抓她走。结果全村人围上来,一人一句反问:
>‘写几个字就犯法?’
>‘难道心里想想也不行?’
>‘你们怕的,是不是我们开始用脑子了?’
>官差愣住,最终未动手。
>现在,每天都有新人来墙上写字。昨夜,有人写了:‘如果法律只保护有权的人,那它还算法律吗?’
>??沈知意留”
阿菱读完,久久不语。她转身看向厅堂角落,发现一处地砖松动。她蹲下撬开砖块,下面藏着一个小陶罐。打开后,是一叠信件,每一封都来自不同地方:云南边境的戍卒,甘肃放羊的老汉,江南织坊的女工,东北伐木的工人……信中内容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提了一个问题,且都说:“我不知道该问谁,但我想让阿菱知道,有人在问。”
她一封封读着,手指微微发抖。有一封信让她停住:
>“我是个刽子手,砍过三十七颗人头。他们大多是‘妄议朝政’的书生。我一直以为自己在执行正义。可上个月,我梦见其中一个死囚转过头,对我说:‘你杀的不是叛贼,是你自己的良知。’我醒来后,再也拿不动刀了。
>我想问:当命令与良心冲突时,服从还是反抗,才算忠诚?
>??一名不敢署名的刑部差役”
阿菱将信折好,收入怀中。她忽然意识到,这场运动早已脱离任何人的掌控。它不再属于她,也不属于沈知意,甚至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或团体。它属于每一个在深夜辗转反侧、心中升起一个“为什么”的普通人。
三日后,她们抵达湖南境内。正值春汛,江水暴涨,渡船停航。她们只得在岸边小镇暂住。镇上有一座百年书院,早已荒废,唯有一间藏书楼尚存。阿菱登楼查阅古籍,试图寻找“天枢教”与“思问之铃”的更多记载。翻至一本残卷《南疆异闻录》时,她发现一段被虫蛀蚀的文字,经辨认后拼凑出如下内容:
>“万历四十年,滇南地震,裂地三尺。有牧童见光自缝出,探首窥之,见地下有室,壁刻万言,皆‘何’字也。室中悬铃,非金非玉,触之无声,然观者脑中自有鸣响。祭司谓此乃‘心钟’,唯大疑者得叩,唯大勇者能听。后朝廷新政,惧其惑民,遣兵填穴,毁铃不可得,遂以铅封之,沉于洱海深处。然民间传言,每逢月圆之夜,洱海之下仍有微光浮动,似铃欲鸣。”
阿菱心头一震。若此铃未毁,只是被封存,那南岭石室中的铜铃,又是何物?是复制品?还是……另一口?
她正思索间,忽听楼下喧哗。奔至窗前,见一群百姓簇拥着一位老妇人而来。那妇人手持一根竹杖,杖头挂着一只破旧铃铛,摇晃时发出沙哑声响。她直奔书院而来,口中高呼:“我知道铃在哪里!真正的铃,还在洱海底下活着!”
众人将她扶上楼。老妇人自称姓陈,乃当年天枢教祭司后人,家族世代守护秘密。她颤巍巍从怀中取出一块青铜片,上面刻着一行小字:
>“双铃并立,一明一隐;一响于山,一鸣于水;若二者同振,则天下无不问之人。”
“什么意思?”有人问。
阿菱凝视青铜片,缓缓道:“意思是,我们找到的,只是‘显铃’。还有一口‘隐铃’,沉在洱海,与之呼应。当两铃共鸣,便是全民觉醒之时。”
消息迅速传开。数日后,竟有上百名“海梦症”康复者自发前往云南,聚集洱海边,日夜守望。他们不做他事,只静坐、冥想、提问。有人写诗:
>“海底有铃谁曾闻?
>但见波涛皆疑问。
>若使千帆载问去,
>不教真理锁深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