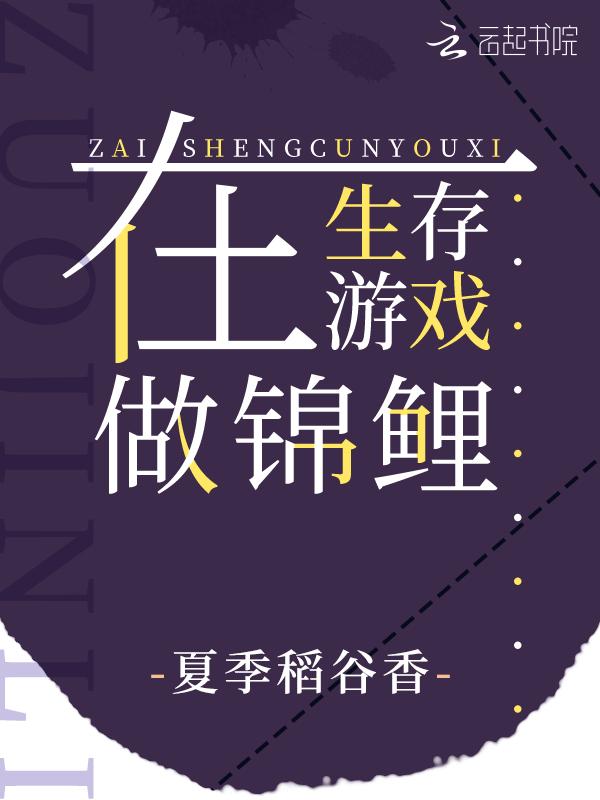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重生侍寢当日,说好的太子不近女色呢 > 第294章 番外12给太子送美人(第4页)
第294章 番外12给太子送美人(第4页)
晚上。
太子有令在先,江平鎧也没敢擅作主张办什么宴,只简单与太子吃了顿便饭便將人送回了下榻的院子。
槛儿没跟去前院。
太子回来时她也刚用完晚膳。
海顺下去用膳了。
太子沐浴不喜人伺候,槛儿伺候完他更了衣,他便自己进了浴间冲洗。
过了会儿。
两个小太监进去伺候太子净髮。
太子从浴间出来时只穿了身天青色软缎寢衣,一头长髮半湿地披著。
他在妆檯前落座。
槛儿忙在他肩背上隔了一层厚布巾子,又替他披了件乾净的外袍。
“现在天气不比七八月份,殿下可得千万当心,不要染了风寒才好。”
她麻利地做著事,一面不忘贴心道。
骆峋看了看镜子里的她,“嗯”了一声。
槛儿笑了笑,专心给他烘头髮。
一通收拾弄罢。
骆峋总算有时间关注小丫头的心事了。
“先回房收拾,完了过来孤有话问你,”他起身往书房走,边走边道。
槛儿下意识想问什么事,被他打断了,“一会儿来了就知道了,去收拾。”
好嘛。
槛儿狐疑地回了耳房洗漱换衣裳。
两刻钟后再过来正房。
太子坐在次间的罗汉床上自己同自己下棋,小几上摆著一碟剥好的橘子。
这会儿十月下旬,南边没有地龙与炕,屋里烧著火盆却是不见得暖。
太子身上披著一件薄夹的大氅,腿上盖著绒毯,长发用一根杏黄色的髮带束著斜搭在左侧身前。
单手撑额,姿態很是隨性慵懒。
槛儿刚走过去,他执棋子的手隨意將那碟橘子推到了她面前,“吃。”
说完对海顺使了个眼色。
不多时,屋里就只剩了槛儿与他。
槛儿看这架势莫名有些紧张,嚼著橘子回想自己这阵子有没有做错事。
正想著,就听对面的人开了口。
“可有什么想问孤的?”
问什么?
问题太猝不及防,导致槛儿有些懵。
骆峋落下棋子撑著额看著她,另一只手探过去用指尖点了点她眉间。
“孤这阵子忙没顾得上你,你是又给自己找愁犯了,真当孤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