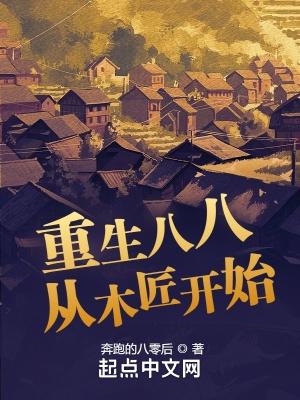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妹宝!別离婚!你老公是阴湿病娇 > 第178章 都惨成这样了还耍流氓(第2页)
第178章 都惨成这样了还耍流氓(第2页)
他將上衣脱下,露出被纱布包裹的精壮身躯,但纱布下,却布满红疹。
他偏过头,看著陈语薇,哑声道:
“来吧。就这样。”
陈语薇抿紧了唇,捏著银针上前,最后提醒道:
“可以,但仅在上身施针,效力最多只能暂时压制住不再恶化,无法引导毒素排出。过程中因为毒素积聚,你会比现在更痛苦数倍。”
“没事。”
季淮深语气平静,甚至带著一丝不易察觉的放鬆。
幸好这样可以。
比这更难熬的他都经歷过,早已习惯。
只要守住他想守住的,这点痛楚,他受得住。
温朵听到“更痛苦数倍”这几个字,心尖都揪了起来,还想再劝。
季淮深却忽然抬眼看向她,努力勾了勾苍白的唇角,试图扯出一个安抚的笑,声音气若游丝,却带著一丝戏謔:
“乖乖,別哭了,也別劝了。你一哭,我这里。。。。。。”
他微颤的手指轻轻按了按自己的心口,
“就跳得又快又乱,慌得厉害。毒气怕是都要被你嚇得上涌,直衝心脉了。”
这话半真半假,夸张得要命,可配上他此刻虚弱又故作轻鬆的神情,却比任何严厉的拒绝都有效。
温朵的眼泪瞬间憋了回去,嚇得连呼吸都放轻了。
她看著银针一根根落下,看著他身体微微痉挛,额际青筋凸起,却死死咬住下唇不肯发出一声痛哼。
只有压抑的、沉重的喘息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温朵的心疼得像要被碾碎。
最终,她再也看不下去,猛地转身,几乎是逃离了这个让她窒息又心碎的场景。
。。。。。。。。。。
温朵跑出房间后,几乎瘫软的滑蹲在走廊角落,她双手抱著膝盖,眼泪啪嗒啪嗒砸在手臂上。
她实在想不通,季淮深为什么要这么固执?
明明都性命攸关了,还坚持什么男女之防。
陈语薇是医生啊,在医生眼里哪分什么男女?
可是。。。。。。想到季淮深苍白却依然强硬的脸,温朵的心又揪疼起来。
他寧愿承受更大的痛苦,也不愿让其他女人看见他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