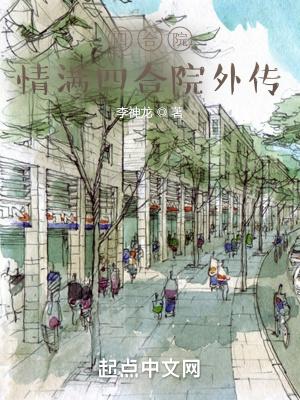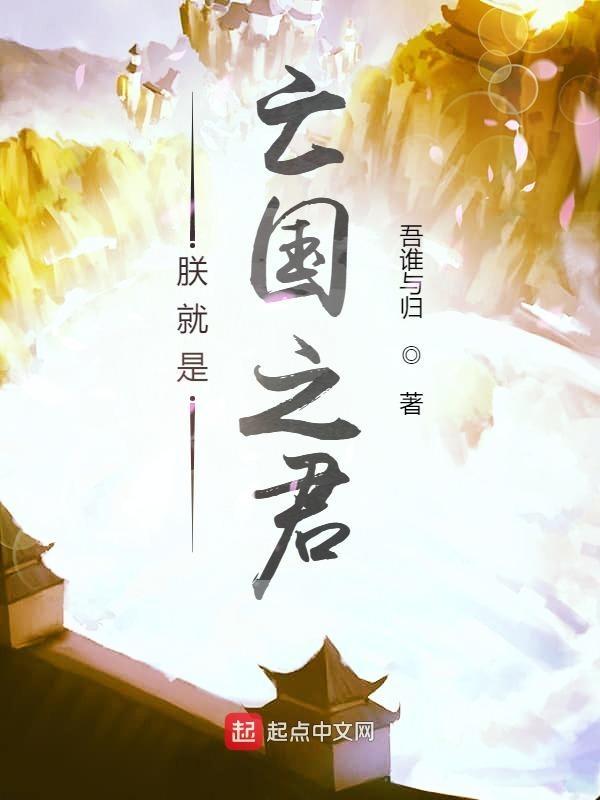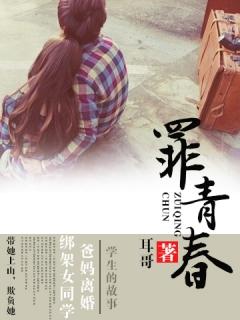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的白月光是受害者 > 为什么还没来(第3页)
为什么还没来(第3页)
天刚蒙蒙亮,沈知秋就抱着她的小羊,再次坐到了那个角落。昨天坐得太久,腿还有些酸麻,但她不在乎。
晨露打湿了她的裙摆,有点凉,她只是把怀里的小羊抱得更紧,仿佛能从这唯一的、真实的馈赠里汲取到对抗清晨寒意的温暖。
手心里,是那朵已经彻底蔫掉、颜色黯淡的紫色小野花,她依旧没有扔掉。
院门每一次被推开,她的脊背都会瞬间挺直,目光像被线牵引着,牢牢锁住门口。
每一次确认不是那个人后,她眼中闪烁的光芒会黯淡一分,但那份固执的期待,却从未真正熄灭。
“她一定会来的。”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声音很小,却很坚定,
“她说过会来的。
她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会骗她,会嘲笑她,会轻易地抛弃承诺。
但那个人不会。那个人带来的糖果是真实的甜,故事是真实的有趣,小羊是真实的柔软。
那么,那句“会来的”,也一定是真实的。
星期一。
她依旧早早地出现在老地方。其他孩子经过时,投来或好奇或不解的目光,甚至有人低声议论:“她还在等那个姐姐啊?”“那个姐姐不会来了吧?”
这些话像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带来细密的刺痛。
但她用力摇头,把那些声音甩开。她低头看着怀里小羊黑色的玻璃眼珠,用指尖轻轻碰了碰。
“她们不懂。”她在心里对小羊说,“你懂的,对不对?她和他们不一样。”
阳光依旧升起又落下,那个人依旧没有出现。期待像被反复拉扯的皮筋,渐渐失去了最初的弹性,但那份源于“坚信”的韧劲,却支撑着她没有断裂。
星期二,星期三……
等待成了她生活中一个固定的、沉默的仪式。她不再像最初那样时刻紧绷着张望,而是抱着小羊,安静地蜷缩在那里,目光时而落在院门,时而落在空无一人的身旁。
她在脑海里反复重温那些周六的午后——那个人平静的语调,那些新奇的故事,指尖短暂的温暖,还有最后那个用力点头说“会来的”瞬间。
这些记忆的碎片,成了她对抗时间流逝和外界质疑的唯一武器。
她开始给怀里的小羊讲故事,用那个人讲述时那种平淡的、安静的语调,复述着她还记得的关于发光鱼、永不落地的鸟和蒲公英种子的故事。声音很轻,几乎只有她自己和小羊能听见。
“它们……不会迷路吗?”她模仿着自己当时提问的语气,然后停顿一下,仿佛在等待一个回答。怀里的小羊安静地看着她。
她在用这种方式,维系着那个即将被漫长等待磨损的“约定”。
院长和阿姨们来看过她几次,试图劝她回屋里,或者去和其他孩子玩。
她只是固执地摇头,抱着小羊的手臂收得更紧,用沉默的背影拒绝所有的劝慰。
她不相信那些人说的话。
她只相信那个人亲口说出的“会来的”。
只要还没亲耳听到那个人说“不来了”,她就愿意等下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希望如同风中残烛,明灭不定。
但沈知秋心里那点由林清阮亲手点燃的、名为“信任”的微弱火苗,却在这近乎偏执的等待中,没有被彻底吹灭。
它摇曳着,挣扎着,支撑着那个坐在角落里的、抱着小羊的瘦小身影,日复一日地,望向那扇始终沉默的院门。
她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但她知道,只要还有一丝可能,她就会等下去。
那群孩子又来了,像每天准时响起的、令人厌烦的噪音。
“沈知秋,你还在等她啊?”为首那个稍大的男孩嗓门总是格外刺耳,他带着他那小团体,围住了蜷缩在台阶上的沈知秋。
沈知秋没有抬头,目光落在自己旧旧的鞋尖上,怀里紧紧抱着那只米黄色的小羊。
台阶冰凉,但这里是那个人坐过的地方,挨着这里,好像就能感觉到一点点残留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