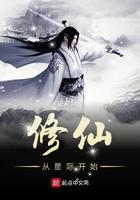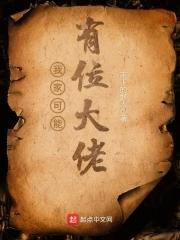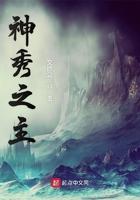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商界女王的复仇之路 > 第149章 海外合作 新局全面开启(第2页)
第149章 海外合作 新局全面开启(第2页)
接下来三天,他们开了五场视频会议。沈知微坐在镜头前,问题直接,不绕弯。瑞士方代表解释决策权问题时,她打断了两次,最后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们的判断,那就别谈合作。”
对方沉默了几秒,答应重新拟定条款。
新加坡公司派来了CEO本人。谈判中,沈知微突然问:“你们去年裁员百分之三十,补偿金是怎么算的?”
那人愣了一下,如实回答了。
她点点头,没再追问。会后对程雪阳说:“这个人说实话,可以谈。”
柏林基金的负责人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全程用中文交流。她说自己在中国待过八年,走过二十多个城市的小企业园区。
聊到最后,她看着沈知微说:“我知道你做过什么。也看到你现在在做什么。我不是来谈生意的,我是来找同行者的。”
沈知微盯着她看了很久,然后说:“下周我去阿姆斯特丹,我们可以继续聊。”
会议结束后,程雪阳整理纪要。沈知微站在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来往的人。
“你觉得哪一家更合适?”他问。
“都不急。”她说,“合作不是救急,是长久的事。”
“可机会不会等太久。”
“那就让它走。”她说,“错一次,就是满盘皆输。”
程雪阳停下打字的手。“你还记得三年前的事?”
她转过身。“我记得每一个细节。”
他没再说话。
第二天一早,沈知微收到柏林基金的新邮件。附件是一份合作备忘录草案,条款清晰,责任分明。最下面一行写着:“我们不要求您改变方向,只希望与您同行。”
她看完,转发给程雪阳。
下午,国际商业协会回信,确认她在峰会上的发言时间:二十分钟,主题自定。
她打开文档,写下标题:“从暴雷到重建:一个受害者的合作准则”。
内容写了整整一天。她写了自己如何被背叛,如何失去一切,又如何一点点找回主动权。最后一段她说:“合作的前提,是双方都能站着说话。如果你发现自己越来越矮,那一定是有人在抽走你的地基。”
晚上八点,程雪阳送来晚饭。她没吃,只喝了杯茶。
“明天还要开会。”他说,“新加坡那边要求见面详谈。”
“好。”她合上电脑,“你订地方吧,安静点的。”
他点头,正要走,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眉头皱了一下。
“怎么?”她问。
“林婉发消息。”他说,“她说有个账户信息,可能对你有用。”
沈知微站起身。“她人在哪?”
“新加坡。但她没说具体内容。”
“让她发给你。”
“她要你亲自确认。”
沈知微盯着手机屏幕,几秒后,拨通了那个久未联系的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你说。”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