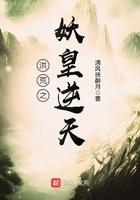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寒门书童:高中状元,你们卖我妹妹? > 第543章 恩威並施北境归心(第3页)
第543章 恩威並施北境归心(第3页)
李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何等正確。
铁路尚未完全贯通,其带来的效益就已经显现。
沿线的城镇,因为工程队的入驻而迅速繁荣起来。大夏的商队,载著精美的丝绸、瓷器、茶叶,沿著已经铺设好的路段深入高丽腹地,又將高丽的布、药材、海產源源不断地运回大夏。
如今,铁路全线贯通,从釜山到汉城,原本需要半个多月的崎嶇路程,被缩短到了惊人的两天一夜。这意味著什么,李琿心中有数。这意味著高丽与大夏,这个庞大帝国的经济命脉,被彻底地连接在了一起。
“殿下,”那名官员又道,“刚刚从釜山港传来的消息,铁路贯通的消息一出,港口外等待入港的大夏商船,已经排到了三里开外!户曹的大人们初步估算,待铁路正式运营,我高丽与大夏的贸易总额,一年之內,至少能激增五倍!”
“五倍……”李琿喃喃自语,这个数字让他心臟狂跳。这不仅仅是財富,更是高丽国力提升的希望,是他稳固王权,推行新政的最大底气。
“传孤的命令,”李琿深吸一口气,目光变得无比坚定,“所有高丽学堂的学员,皆可申请进入铁路沿线的各个站点,担任技术官吏。另外,再向大夏京城的皇家理工学院,追加十个公派留学的名额!钱,从王室的內帑里出!”
他要让整个高丽的年轻一代都看到,学习新学,为国效力,才是真正的出路。
就在李琿为高丽的未来擘画蓝图之时,一艘悬掛著三叶葵家纹的倭国海船,正乘风破浪,仓皇地驶向江户。
数日后,一名信使面色惨白地跪在德川家康的面前。
“主公,高丽……高丽人的铁路,通了!”信使的声音带著颤抖,“从釜山到汉城,两天!大夏的货物,两天就能铺满汉城的市场!他们的贸易额,据说……据说要翻五倍!”
德川家康端坐著,苍老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但那双微微眯起的眼睛里,却闪烁著骇人的精光。他面前的茶杯,水汽裊裊,但他却久久没有端起。
“五倍……”他缓缓吐出这两个字,声音沙哑。
自从被大夏击败,他选择臣服,担任大夏倭国总督府的副总督以来,德川家康无时无刻不在感受著那座大陆上传来的巨大压力。
他曾以为,只要自己足够恭顺,只要倭国能为大夏提供稳定的白银和硫磺,就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他甚至为自己成功保全了德川家的基业而感到一丝庆幸。
可高丽的崛起,给他带来了危机感。
同为大夏的藩属,高丽人却走在了前面。他们不仅学习大夏的制度,更引进了大夏的技术。铁路!那是何等恐怖的东西!
德川家康亲眼见过大夏总督丁远大人桌上的沙盘,那一条条红线,將庞大的帝国串联成一个整体,皇帝的意志,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內,抵达任何一个角落。
现在,这条红线,已经延伸到了高丽。
而倭国呢?依旧是那个分裂、落后,依靠海路进行缓慢交通的岛国。长此以往,高丽將远远把倭国甩在身后。在大夏皇帝的眼中,一个繁荣、高效、能提供更多价值的高丽,和一个落后、守旧、只能提供矿產的倭国,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他甚至能想像到,未来某一天,大夏皇帝会因为倭国的“无用”,而毫不犹豫地將之拋弃,甚至……更换一个更“有用”的代理人。
危机感,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笼罩在德川家康的心头。他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不能再这样被动地等待下去。
“庆,”他忽然开口,唤著自己儿子的名字。
“父亲大人。”一名身穿大夏儒生服饰的年轻人,从屏风后走出。他便是德川庆,德川家康最寄予厚望的儿子。此人曾在大夏京城留学三年,深受新政思想的影响,举手投足间,已经褪去了倭国武士的影子,更像一个大夏的文人。
“你对高丽之事,如何看?”德川家康问道。
德川庆躬身道:“父亲大人,孩儿以为,高丽之兴,非高丽之能,实乃大夏之功。李琿世子所行之事,无一不是在效仿大夏。他抓住了根本,那便是『变』。顺应大夏而变,则兴;固步自封,则亡。”
“说得好,”德川家康点了点头,“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变』?”
德川庆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著自己的父亲:“父亲大人,我们不能再等了。孩儿恳请,亲自率领使团,再赴大夏京城!我们不能只满足於缴纳贡品,我们要向高丽人一样,向大夏求学,求技术,求一条能让我们倭国也脱胎换骨的道路!”
他顿了顿,声音里带著一丝激动:“孩儿在大夏时,曾听皇家理工学院的先生们说过,皇帝陛下曾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今,大夏便是这股潮流!我们与其被动地被潮流吞没,不如主动地,匯入其中!”
德川家康沉默了。他看著自己的儿子,这个在大夏待了三年,思想已经完全“华化”的儿子。他心中五味杂陈,有欣慰,也有著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哀。但他知道,儿子是对的。
“好。”许久,他终於开口,只说了一个字。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著窗外江户城的天空。
“去吧,”他背对著德川庆,声音苍老而坚定,“告诉大夏的皇帝,我德川家,愿意献出所有,只为让倭国,能跟上他的脚步。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德川庆重重地跪下,叩首道:“孩儿,定不辱使命!”
他知道,他此行背负的,將是整个倭国的未来。而他要去见的,是那个亲手终结了战国时代,如今又在亲手塑造整个东亚格局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