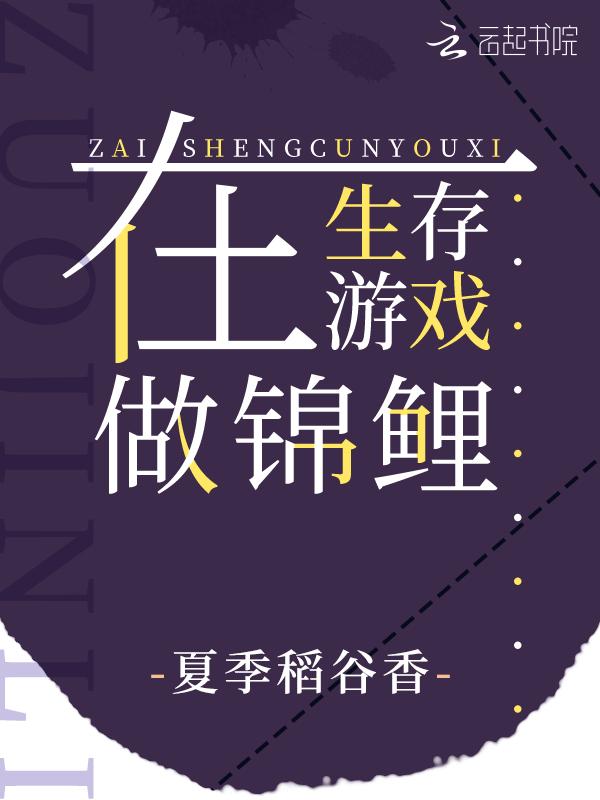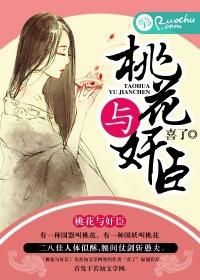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从学生成就霸业 > 第369章 铁轨长杀意浓(第2页)
第369章 铁轨长杀意浓(第2页)
眼镜蛇笑了笑,那颗痣跟着跳了跳:“江湖规矩,人死账消。但你不该杀小刀,他是我奶娘的儿子。”他弯腰打开皮箱,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沓沓钞票,用红色的纸条捆着,“这里有五百万,你拿着,带着这老东西和你的猫走,永远别回这座城市。”
火狐狸突然对着他龇牙,喉咙里发出威胁的低吼。我盯着那些钞票,突然想起三年前那个雨夜,我蜷缩在垃圾桶旁,看着酒吧里醉醺醺的客人把钱撒在舞池里,而我连块面包都买不起。
“我要的不是钱。”我缓缓摇头,目光扫过他身后的壮汉,“虎爷账本上那个副局长,还有张秃子,都得付出代价。”
眼镜蛇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他从皮箱里抽出一沓钞票,用手指弹了弹,“这城里一半的警察靠我吃饭,一半的混混听我调遣。你杀了虎爷,我可以当没看见,但你想动我的人?”
他突然把钞票扔在地上,用皮鞋碾得粉碎:“年轻人,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你以为杀了几个小混混就了不起?在我眼里,你跟这铁轨上的蚂蚱没区别。”
李医生突然往前一步,尽管脸色惨白,腰杆却挺得笔首:“陈立东,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没人知道?当年你为了抢地盘,放火烧死的那家人,尸骨还埋在城西的地基下!”
眼镜蛇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那颗痣像颗血珠似的凸起来:“老东西,你找死。”他抬了抬手,身后的壮汉立刻举起短铳,枪口齐刷刷对准李医生。
“别动他!”我把李医生拽到身后,开山刀指向眼镜蛇,“有什么冲我来。”
火狐狸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啸叫,猛地窜向最近的那个壮汉。那家伙刚要扣动扳机,手腕就被火狐狸死死咬住,短铳“哐当”掉在铁轨上。旁边的壮汉立刻调转枪口,我想都没想就扑了过去,用身体挡住火狐狸。
“砰!”
枪声在空旷的铁轨间炸开,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子弹擦着我的胳膊肘飞过,打在后面的信号灯上,迸出一串火花。我趁机抄起地上的短铳,对着那壮汉的膝盖扣动扳机。
又是一声枪响,那家伙惨叫着跪倒在地,血顺着裤腿流进铁轨缝隙里。其他三个壮汉立刻开枪还击,子弹“嗖嗖”地从我耳边飞过,打在钢筋上溅起火星。
“走!”我拽着李医生往涵洞跑,火狐狸叼着我的裤腿跟上。眼镜蛇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点气急败坏:“给我打死他们!谁活剥了苏然的皮,城东的地盘就给谁!”
涵洞深处一片漆黑,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和喘息声在回荡。我摸出打火机点燃,火苗在风里摇摇晃晃,照亮洞壁上斑驳的涂鸦,大多是些帮派的标记和骂人的脏话。
“这边!”李医生突然拽了我一把,指向涵洞侧面的一个裂口。那里大概是当年施工时留下的,仅容一人通过,里面黑得像泼了墨。我先把李医生推进去,然后让火狐狸跟上,自己最后钻进去时,衣角被石头挂住,撕拉一声裂开个大口子。
刚站稳脚跟,就听见外面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叫骂声。有人用手电筒往涵洞里照,光柱在洞壁上扫来扫去,离我们藏身的裂口越来越近。
“屏住呼吸。”我捂住李医生的嘴,另一只手紧紧攥着短铳。火狐狸趴在我脚边,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尾巴紧紧夹在两腿之间,这是它紧张时才有的样子。
光柱突然照在裂口处,晃得人睁不开眼。外面传来个粗哑的声音:“蛇哥,这边有个缝,会不会藏在里面?”
“炸了。”眼镜蛇的声音隔着石头传过来,带着股狠劲,“给我用炸药,别留活口。”
我的心猛地一沉。这裂口是用预制板和石头砌成的,根本经不起炸药炸。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对讲机,突然有了个主意,拽了拽李医生的胳膊,指了指裂口深处——那里似乎还有条狭窄的通道,不知通向哪里。
“你先走,我断后。”我低声说,把牛皮笔记本塞给他,“记住,去找老周,拿到账本就寄给省纪委,别回头。”
李医生还想说什么,我己经推了他一把,然后拍了拍火狐狸的头:“跟着李医生,保护好他。”火狐狸蹭了蹭我的手心,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钻进了深处的黑暗里。
我深吸一口气,握紧短铳,突然从裂口跳了出去,对着最近的那个壮汉扣动扳机。枪声在涵洞里炸响,震得石头簌簌往下掉。那家伙惨叫着倒下,其他人立刻调转枪口向我射击,子弹打在我身边的石头上,迸出密集的火星。
我借着混乱滚到涵洞口,抓起地上的根钢管,对着堆在旁边的废弃木箱狠狠砸过去。箱子里不知装着什么,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趁这功夫,我摸出对讲机,调到之前听老鬼说过的紧急频道,按下了通话键。
“城东货运站,涵洞,眼镜蛇带着炸药……”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颗子弹打断了。子弹擦过我的肋骨,火辣辣的疼,像是被烙铁烫了一下。我踉跄着冲出涵洞,往铁轨深处跑,身后传来眼镜蛇的怒吼:“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铁轨在脚下延伸,像是没有尽头。远处的信号灯不知何时全部亮了起来,红光在铁轨上拉出长长的影子,把我的身影撕成一片一片。我能听到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能闻到空气里弥漫的硝烟味和血腥味,还能感觉到肋骨处的伤口在流血,浸湿了衬衫,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
突然,前方的铁轨开始震动。不是摩托车,是火车!震耳欲聋的鸣笛声从远处传来,灯光像两颗太阳,刺破风里的烟尘,越来越近。
我回头望去,眼镜蛇带着人追了上来,他手里举着把短铳,枪口正对着我的后背。我突然笑了,转身迎着火车的灯光跑过去,张开双臂,像只即将展翅的鸟。
风里传来火狐狸的啸叫声,大概是从远处的黑暗里传来的。我想起三年前那个雨夜,李医生把半根烟塞给我时的样子,想起王姨端着热汤面站在门口的样子,想起火狐狸第一次跟着我时,怯生生地蹭我手心的样子。
原来有些疼,不是为了让人记住,是为了让人明白,有些东西,比疼更重要。
火车的鸣笛声盖过了所有声音,灯光把我的影子投在铁轨上,拉得很长很长。我看见眼镜蛇的脸在灯光里扭曲,看见他扣动扳机的手指,然后纵身一跃,跳向铁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