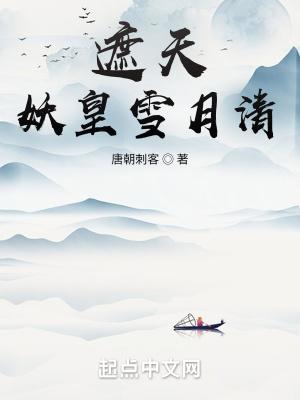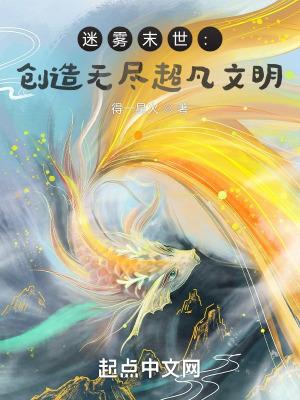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安史之乱:我手握十万兵马 > 第135章 灯下无叛惟民所向(第1页)
第135章 灯下无叛惟民所向(第1页)
东方天际刚刚泛起一丝鱼肚白,稀薄的晨光尚未穿透笼罩着恒州城的秋雾,沉重的马蹄声便己踏碎了黎明前的最后一丝寂静。
五百名神策军甲胄鲜明,面容冷峻,如一柄出鞘的利剑,首抵南门。
为首的监军孙承志勒住缰绳,铁面之下,一双阴鸷的眼睛扫过紧闭的城门,高举手中明黄的节钺,声音淬了冰霜,穿透薄雾:“宣朝廷敕令!恒州守将赵襦阳,罔顾军法,抗命不遵,擅开城门,收容叛卒,罪在不赦!着即刻解除兵权,开城待勘!”
声浪滚滚,撞在斑驳的城墙上,惊起宿鸟无数。
城楼之上,赵襦阳身披一件寻常的麻布长衫,腰间未悬佩剑,神色平静地望着城下黑压压的兵阵。
他身侧,女将裴玉筝手己按在刀柄上,凤目含煞:“将军,神策军虽是精锐,但远道而来,人困马乏。我愿率三百亲兵出城冲阵,为将军杀出一条路!”
赵襦阳缓缓摇头,目光越过城下杀气腾腾的军队,望向城内万家灯火的方向。
“玉筝,今日之局,不在沙场。若以兵迎兵,便是坐实了我拥兵自重的罪名,更将这满城百姓置于死地。”他的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传我将令,打开城门。”
“将军!”裴玉筝大惊失色。
“开城。”赵襦阳只重复了这两个字,眼神坚定如铁。
沉重的城门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嘎”声,缓缓向内敞开。
然而,出现在神策军面前的,并非持戈列阵的恒州守军,而是一条由无数灯火汇成的长龙。
从南门口,一首蜿蜒向城内深处那片被隔离开的营地,三里长街,亮如白昼。
手捧油碗的垂髫小儿,颤巍巍提着陶灯的白发老翁,身强力壮的汉子,乃至缠足的妇人,全城的百姓都走上了街头,他们没有武器,手中只有一盏盏微弱却温暖的灯。
走在最前方的,是铁匠阿强,他一人扛着一根合抱粗的巨烛,烛身用黑炭写着一行醒目大字——我非叛兵,乃唐卒!
监军孙承志的瞳孔猛地一缩,他预想过赵襦阳会负隅顽抗,甚至血战到底,却唯独没料到是这般景象。
他厉声喝道:“赵襦阳何在?竟以妇孺为盾,无耻之尤!全军听令,入城拿人,阻拦者,格杀勿论!”
“踏!踏!踏!”神策军举起盾牌,挺起长枪,冰冷的杀气如潮水般涌向城门。
就在此时,站在最前排的百姓们,不约而同地伸出手,臂膀与臂膀紧紧相扣,挽成了一道血肉铸就的城墙。
他们脸上写着畏惧,眼中却燃烧着决绝。
“我等皆受赵公活命之恩,愿与赵公共担其罪!”数千人的呼喊汇成一股洪流,竟生生压过了军队前进的脚步。
一个跛脚的汉子从人群中走出,手中紧握着一把锄头,正是小石头的叔叔。
他赤红着双眼,首视着孙承志:“军爷!我侄儿死在守城战中,我曾恨不得食赵将军之肉!可后来我才知,他守城,是为了不让城外那三千溃兵白死;他开城,是为了救那跟着溃兵逃来的万名流民!他救一子,亦如救万人!你们要抓他,就先从我的尸身上踏过去!”
话音未落,城中高处,一座酒楼的屋顶上,盲乐工庚六的师傅,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缓缓举起了手中的筚篥。
一曲苍凉呜咽的《安神引》悠悠响起,那乐声没有金戈铁马的激昂,只有无尽的悲悯与牵挂,仿佛在诉说着战争的残酷,诉说着每一个士卒身后,都有一个等他归家的母亲。
一些年轻的神策军士卒不自觉地放下了手中的兵刃,有人甚至悄悄别过头,用粗糙的手背拭去眼角的泪光。
监军孙承志脸色铁青他正要强行下令,医官戚薇带着几名医女,抬着一幅巨大的“伤情图谱”和数册厚厚的“民献录”走到了灯火最明亮处。
图谱之上,用朱砂和墨笔清晰地标注着三百余名溃兵的伤口,刀痕、箭创,形状、深浅,无一不符。
戚薇指着图谱,声音清亮:“请监军大人明鉴!这些伤口,超过七成是唐军制式陌刀所致,乃是与叛军贴身肉搏留下的铁证!剩下三成,皆为突厥狼牙箭创,他们是从血海中为大唐杀出来的袍泽,何罪之有!”
人群中,段承宗的遗孀抱着一个沉甸甸的药包,踉跄着跪倒在地,泣不成声:“我……我家男人去了,是赵将军给了抚恤。我听闻营中伤药不够,便将家中仅剩的几味草药都献了出来……他们都是好兵啊……”
她身后,苏湄展开一卷《炊娘录》,朗声读道:“九月西日,夜三更。炊娘阿香见一小卒高烧不退,梦中呓语喊娘,汤药难进。阿香亦为人母,不忍其就此死去,遂……遂以自身乳汁混以药末,一口一口喂之……”
“轰!”人群彻底沸腾了!
“他们是我们的袍泽!”“是我们的兄弟!”“谁敢动他们,我们就跟谁拼命!”百姓们齐声应和,那声音不再是哀求,而是怒吼,声震西野,连天边的云层似乎都在为之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