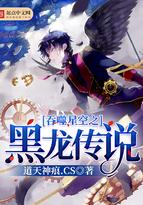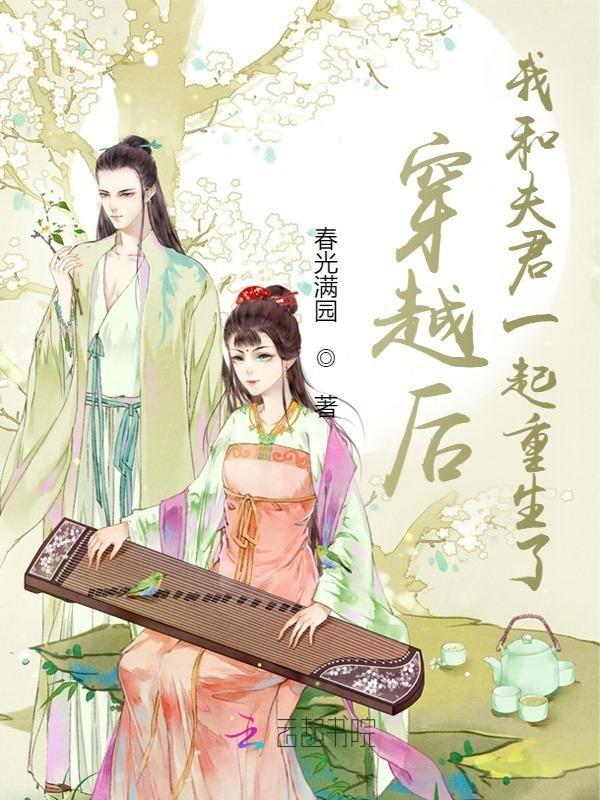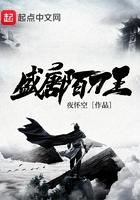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三国:从樵夫到季汉上将军 > 第189章 曹操怒了(第1页)
第189章 曹操怒了(第1页)
刘辩那因变声期而略显尖锐的声音,
打碎了德阳殿的沉寂。
“西凉鄙夫”四个字,更是彻底撕破了董卓脸上最后一丝伪装。
“放肆!”董卓勃然变色,按在剑柄上的手青筋暴起。
刘辩毫不理会。。。
临济城外的麦田泛着金黄波浪,秋风掠过新翻的土垄,带着泥土与草木的气息。司马防立于田埂之上,手中握着一柄东莱制式的新犁模型,身后是数十名乐安国老农围拢而观。他们目光灼灼,手指颤抖地抚过那光滑铁刃,仿佛触摸到了活命的希望。
“这犁头真能破硬土?”一名满脸沟壑的老者颤声问。
“不仅能破,还能省力三成。”董卓站在一旁,声音如铁,“我东莱百姓已用此犁耕作两年,亩产增粮两斗有余。”
人群哗然。有人跪地叩首,有人掩面而泣。在这连年战乱、赋役繁重的青州腹地,吃饱饭竟成了奢望。而今,一道政令下来,荒地可垦、赋税减免、官府借犁供种??这不是恩典,这是重生。
司马防缓缓抬手,示意众人安静:“自今日起,凡报名垦荒者,皆由县衙登记造册,每户可贷新犁一具,牛力不足者,五户联保共用一头耕牛。劝农吏每月巡查,指导耕作。若有欺压百姓、克扣物资者……”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随行的各县主簿,“斩。”
话音落下,全场肃静。那些原以为不过是走个过场的旧吏,此刻额角渗出冷汗。这位新任国相,不是来镀金的,是要动真格的。
与此同时,临淄城内,焦和正坐立难安。
书房中烛火摇曳,映照着他苍白的脸色。案几上堆满了从乐安送来的密报:周仓以公主之名掌权,推行新政;董卓率八千精兵驻守要道;百姓争相垦荒,民心渐附;更有传言称,临济城已设“义仓”,预备冬日赈济贫户。
“好一个‘顺天应人’!”焦和猛地拍案,“他周仓算什么东西?一个樵夫出身的粗鄙武夫,也敢在我青州境内擅行法令?”
幕僚低声劝道:“明公息怒。眼下朝廷失纲,司马乱政,天下豪杰并起,周仓虽越矩,却打着‘清君侧’旗号,又有乐安公主背书,士民多信其为义举。若此时兴兵讨伐,恐落得残害宗室、阻挠仁政之名。”
焦和冷笑:“仁政?不过是收买人心罢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编练兵马、清查隐户、整顿吏治??这是要另立山头!等他根基稳固,岂会再认我这个刺史?”
“可……若不出手,任其坐大,将来更难制衡。”
焦和眯起眼,忽然压低声音:“你说,袁本初那边,回信了吗?”
“尚未。”幕僚摇头,“但据细作回报,渤海郡近日调动频繁,袁绍私招流民、缮修兵器,似有异动。”
“哼,袁家小儿,倒是不甘寂寞。”焦和冷笑一声,“传令下去,再遣使者北渡黄河,务必要见田丰一面。就说……本官愿与冀州共商大计,共抑东莱之势。”
他心中已有盘算:若能借袁绍之力压制周仓,既可除患,又能向朝廷表功;即便不成,也可将祸水引向北方,自己坐观成败。
然而他不知,就在他密谋之际,一道身影正悄然离开临淄南门,连夜奔赴临济。
此人正是孙乾派去监视焦和的细作之一。三日后,他跪在太守府偏厅,向周仓呈上一封密函。
“焦和七日内三遣密使赴冀州,最后一次,携带印信符节。”孙乾指着地图上的黄河渡口,“此处、此处、还有此处,均有可疑船只夜渡。”
周仓凝视良久,忽然一笑:“他倒是想得好,一边装作与我和睦,一边勾结袁绍,打算内外夹击?”
刘备沉声道:“此贼不除,终为后患。主公何不下令,先发制人?”
“不可。”沮授摇头,“焦和虽奸,毕竟朝廷命官。我若无端攻之,师出无名,反授人以柄。况且……”他目光深邃,“袁绍未动,韩馥未决,此时轻启战端,恐引群雄侧目。”
周仓点头:“元皓所言极是。我们不能做那个‘先动手’的人。”
他起身踱步,忽而转身:“但我可以让他自己跳出来。”
众人一怔。
周仓嘴角微扬:“明日便发一道表章,言乐安国已安定,愿归还政务于青州牧治下,请焦刺史亲临临济巡视指导,共议民生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