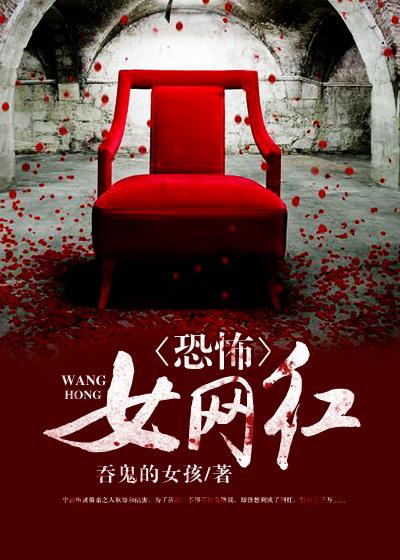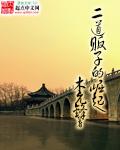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 第165章 热门选手(第6页)
第165章 热门选手(第6页)
她的手指在光下像是不触键的一串影子,连贯得几乎没有重心,只见到起伏,看不到发力。
观众情绪从最初的专注,变成压抑的惊叹。
他们不是被震撼,而是因为一个事实被迫沉默。
这个少女的技术没有任何可挑剔之处。
画面在每个人心中不约而同地出现:
晴冬的早晨,薄霜挂在树枝上,微风吹过,霜屑轻轻坠落,发出细碎的脆响。
并不炫目,却让人无法忽视那份纯粹。
第三段的高音泛起时,整个厅像被提起。
不靠力量,也不靠冲击性,而是靠整个音区的均匀明亮,使人产生一种稳稳升空的错觉。
曲子结束得极干净。
像是最后一粒亮点落在深处,再无回音。
空气停了半秒。
那半秒里,所有人都在重新确认自己听到的东西。
之后,掌声并不喧哗。
却密集、坚定、毫不犹豫。
这不是“被震撼”的表现,
而是对一个事实的承认。
她是实力远超年龄的选手。
这首钟,她没有把它当成炫技,而是把它当成一种极纯的亮色,在众人面前展开。
四、拉赫玛尼诺夫《音画练习曲》Op。39No。5
她刚把手从钟的最后一个跳音上收回,琴声还在空气里轻轻颤着。
但她没有停顿太久。
只是轻轻吸了一口气,坐姿微调,手臂放松,再抬眼时,整个人已经进入另一种密度。
观众席里安静得异常。
听得出,很多人其实还沉浸在上一首的辉煌余波里。
可当她落下第一组和弦时,那种未散尽的余韵瞬间被压下,像一块巨石落进深井。
这首练习曲跟之前的任何一首都不同。
不是飞翔,也不是光亮,而是一种沉重、逼近,带着深海压力的暗潮。
琴声一下子变得厚。
不同于宏大,而是像夜色下的深林,黑得没有形状,却在悄无声息地拉近视线。
她的触键并不暴躁。
那是精确的重量,控制得极稳,不慌不忙。
每一下落键像是从胸腔深处推出来的低频冲击,让人下意识屏住呼吸。
她处理低音的方式很独特。
不是简单的铺陈,而是让它像地层一样缓慢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