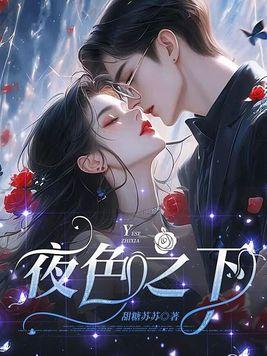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重生之我要拿下肖赛冠军 > 第164章 继续(第5页)
第164章 继续(第5页)
音色轻亮,像在一块小而薄的银片上,余音干净不拖尾,让整首曲子一开始就显得异常明晰。
她的右手动作极轻,指尖从键面略略擦过,像在绷紧的空气上刻下点点亮光。
左手的支持低而稳,不抢位置,只是让右手的跳音像被托起一样往高处跃。
速度并不急,她明显是在控制每一次触键的落点,让那种出名的铃声质感真正落成。
音与音之间没有杂音,也没有擦碰感,像水滴敲在玻璃边缘。
听众的脑海里开始浮起画面。
有人感觉像在看透明的风铃,被一阵轻风挑起;
有人听见了高处教堂的清晨敲钟声,被雾气包围着,明亮而遥远。
还有人感觉到一种近乎孩子气的纯净跳跃,仿佛阳光在石板路上跳动。
情绪迅速被点亮。
从刚才拉威尔的深海与危险里抽离出来的人,像是一下子被带到了清朗的高空,呼吸变得明快。
曲子进入中段时,她的技巧显露出一种不费力的轻盈,每一次快速跳键都像提前知道了落点。
右手高位的连串跳跃既精准又松弛,没有任何生硬的推拉,每粒音像被提前磨过一样干净。
这些细节让懂行的观众一下就坐直了。
练习曲的难点从来不是速度,而是轻。
而她的轻,是建立在极稳基础上的轻。
像柔风,却不是弱风。
像敲击,却不带重量。
这种控制让不少听众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那是对熟练技艺的认可。
尾声的回环段落被她处理得近乎透明,每一串上行跳音都像被描在空白之上,弧线准确,亮度统一。
当最后一串高音敲落时,台下出现一瞬间的凝滞,随后有些听众轻轻吐息。
不是解?,而是被那种纯粹轻亮的技巧打动后的自然反应。
曲子结束,空气仿佛亮了一度。
这首短小却危险的作品被她处理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铃声世界,明亮、轻巧、完整。
观众席里有人轻轻点头,认可那种不花哨也不炫耀的技艺。
她不是在表现力量,而是在展示一种彻底掌控后的自由。
在座的人都清楚,这首曲子若弹不好会变得琐碎而凌乱,而她让它变成了一片收束了所有亮光的清朗天空。
第四首:肖邦《叙事曲》第三号Op。
观众在她换谱、短暂停顿的瞬间重新坐定。
午后的灯光从高处落下,把舞台照得干净、锐利,像一张被摊平的白纸。
他们已经听了三首技巧和色彩密集的作品,本该有些疲惫,但在她抬起头,手落向键盘的时候,又不自觉地挺直了背。
她的神情似乎也在改变。
之前是技巧与幻想的精巧,现在像是把所有浮动的光收起来,让注意力沉进更深的地方。
这种转变让观众产生了一种安静的预感:这首曲子可能不是炫技,而是讲述。
第一个和弦落下时,空气轻轻收紧。